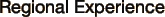
2004年泰國健康農業之旅
文/舒萌 楊皓二零零四年三月,應香港社區夥伴之邀,楊皓和我作為瀚海沙的成員,踏上了這次考察泰國有機農業的旅程。我們想去看看同樣是東方民族,同樣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同樣面臨著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衝擊,同樣帶著傳統漸漸衰退的憂思,泰國的農民與民間團體是如何在實踐中保持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平衡。
山中的隱居歲月
雲婉畢業於曼谷一所著名大學的法律系,之後卻一直從事與農業相關的工作。先是在一個民間團體中進行農作物遺傳資源的保護,後來又和丈夫一起去到泰國西部的山區中,開創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初識雲婉是在去年的北京,一個另類有機農業的經驗分享會上。她笑聲爽朗,讓人印象深刻,樸素熱情的臉上完全找不出法律系高材生的痕跡。我問她為什麼喜歡種地,覺不覺得辛苦,她說自己本來就是一個農民。我們談到她在做的事情,談到她的孩子,她的農場和小木屋,當時還覺得是很遙遠的故事。想不到幾個月以後,我們到泰國的第一站就是雲婉的家。在連綿的青山中穿行,經過村子裏的幾戶人家,再拐幾個彎下一道緩坡,就到了雲婉的農場。一路上到處是草木蕃秀的熱帶風光,隨處可見竹木結構的高腳屋。村裏的人看見雲婉,都微笑著跟她打著招呼。與我之前想像的一個做研究示範用的"正規"農場相去甚遠,沒有大片橫平豎直規劃嚴整的田地,沒有太多現代化的設備,三間傳統樣式的木屋,一小排簡單乾淨的廁所,兩口大肚子的紅色水缸,奔跑嬉戲的孩子和狗——正是山林中一戶幸福美滿的人家。
我走到幾竿合抱的綠竹旁,仰起頭細細看她們,比起溫帶的竹子,她們可高大粗壯多了。一條小小的溪澗從旁邊流過,蜿蜒到更深更遠的地方。不遠處,有一座別具風格的茅草亭子,我走過去,看到一個大約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正在擦它的欄杆,身上的舊衣服沾著泥土。他停下來用英語告訴我可以坐在這裏乘涼,黧黑的臉膛上有一種憨厚誠實的表情,略帶靦腆。我心裏想,這大概是附近村子裏來幫忙的農民吧,可能是跟雲婉學的英語。直到中午吃完飯後,我才弄明白他就是雲婉的丈夫——帕翁先生。
下午,我們就坐在綠竹旁的石凳上,聽帕翁為我們介紹當地的情況:這裏位於泰國西部的邊境山區中,與緬甸交界,原本是一片原始森林,緬甸的克倫族原住民世代居住於此,採集林中的花果,過著遊耕的生活(一塊地種一段時間就休耕轉移,過幾年再輪轉回來)。大約十年前,政府和大公司來到這裏開始大規模的伐木,打破了克倫族人原本自給自足的平靜生活。首先是修進來的公路帶來了所謂的"現代化",人們的消費欲望被刺激起來。以前,他們會種很多種類的糧食蔬菜,還有一些藥用植物,用在自己的醫療體系中。而現在,為了掙到更多的錢,大家開始單一種植玉米、苜蓿一類的經濟作物,越來越多的依賴於外面的貿易市場。而天災和市場的變化都會影響他們的收成,往往導致很多人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同時,由於森林被破壞,土地河流被種植經濟作物時使用的大量農藥化肥所污染,克倫族人幾百年來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也不再能提供給他們足夠的資源。在帕翁和雲婉到來之前,村民們有的非法伐木,有的靠打獵維生,有的不得已離開家到外面去打工,也有人搬到更深的森林中去種植大麻或是更多的經濟作物。
帕翁告訴我們,他自己可以算是本地人,因而當看到這些情況時,便希望能在當地做一些事情。相較於比較流行的"支農"工作而言,回到家鄉本土,更是自己身體力行探尋鄉村發展之路。這條路上,還有本鄉長者可以請教,還能憶起父輩兒時的叮嚀。於是,他和雲婉一起回到這裏,成為一個家庭組織,既是生活,也是工作——在生態已經被破壞的情況下利用現有的條件,依靠本地人保護自然與文化資源;通過推動生態農業幫助村民們解決生計問題,同時協助復興本土文化知識,並將其應用在社區發展上。這些事情,他們已經做了十一年。
帕翁對於村民來說像是一位導師,後來我們在與村民的交談中感受到,這個導師既是實際意義上的,也是精神意義上的。具體來說,他鼓勵大家從常規耕作(使用農藥化肥)轉變成有機耕作,一方面在自己的農場上加以實踐,同時也教授感興趣的農民可持續農業的技術,幫助他們規劃農場,防治病蟲害,提高產量。這種課程除了幾天的理論課與附加的讀寫課外,大部分是在實踐中完成,類似於我們所說的田間學校。在教課的同時,帕翁也會跟學生分享他的生活哲學,交換各自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在這樣的過程裏,學生們漸漸開始思考貧困背後的原因,對於可持續農業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第一代的學生中又會有人成為後來者的老師,使這種教學可以在村民中間自己展開。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了第三代學生。他們還組成了自己的協會,相互合作,分擔責任。帕翁認為可持續農業首先應該能夠提供足夠的糧食給農民自己,同時也能有一部分經濟作物用來換取現金,應付生活的需要。因此,他和雲婉也會和一些團體合作,幫助村民們到附近的市場推銷農產品。
除此以外,雲婉更喜歡和村裏的婦女在一起,研究傳統的染色與編織工藝。不必從外面請什麼專家,女人們只是聚在一起,回想媽媽以前怎麼做女紅,怎麼用天然的植物和礦物染布,然後加以實踐和完善。通過賣出這些家庭手工藝品,可以賺到一些錢補貼家用,更重要的是她們不必再像以前那樣要到外面去打工。現在,她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家庭。而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恢復自己的工藝,自然是讓人相當快樂的事情。帕翁告訴我們,雲婉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做了一些協調和記錄的工作,所有的研究都是由當地婦女自己來完成。帕翁是謙遜的,做這些工作需要用心,一定有很多時間和精力投入其中。而這一類事情,他們都是不收錢的。兩人的生活基本是靠項目支持的研究活動和一些零散的顧問工作來維持。帕翁說,他不願意從自己的學生和鄉親手裏賺錢,那樣違背他的原則。
我回頭看了看坐在後面的雲婉,她懷裏抱著最小的兒子,正呢呢細語地哄他睡覺。在帕翁講述的過程中,她始終沒說什麼,只是望著我們微笑。雲婉也是謙遜的,我從沒聽她說過自己有多麼辛苦,做了多少事情——除了這些工作外,她還是四個男孩的母親,還要在其他團體裏開展一些志願者的活動。以後幾天的行程她一直陪伴著我們,默默照顧大家,做各種協調聯絡的工作,及至分別卻反而向我們道謝,說她在交流的過程中受到很多啟發。
或許謙遜的人更容易向下看,看到一些樸素而易行的方法,不需要有很多錢和現代科技就可以完成。帕翁夫婦只是用心創造了一些地利人和的條件來恢復千百年來的農業傳統,就讓很多邊緣農民重又能安居樂業。無獨有偶,一個印度的農業科學家也說過:"我們所教授的知識都是當地農民幾百年來以某種形式一直在從事的方法。我們所做的只是把這些知識搜集起來,讓它變得更容易運用"。很可惜,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後來只去附近拜訪了幾位農民,而婦女們一起做傳統手工藝的情景始終沒有機會看到。
從村子裏回來,我們在農場新建的木屋中度過了一夜。在我睡下的時候,雲婉還在為大家磨豆漿,準備明天的早餐。帶著微微的歉意,呼吸著山中清新的空氣,我漸漸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清晨,帕翁帶我們參觀了整個農場,並示範給我們如何利用廚餘和落葉堆肥。在這裏,所有的剩飯剩菜,瓜果皮屑都是寶貝,通過簡單的方法變成最好的肥料。在一棵大樹下,帕翁撥開堆積的樹葉和土的混合物,給我們看裏面已經在分解的葉片——樹木把土裏的養分抽上來,透過葉子再還回大地,自然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經過帕翁的介紹,我才猛然醒覺,這個看似平常的小農場其實能將各種資源都充分利用起來,形成一個平衡運轉的循環系統,絕少浪費,實得益于主人運籌規劃之功。後來我們還發現在廚房的屋簷下,有幾根用作收集雨水的管道,通到蓄水缸中。便想起《孝經》中所說:"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參觀完農場,我們坐下來一邊吃早飯一邊聊天。雲婉在豆漿裏放了當地的一種大蔥,喝起來特別香。同行的李榮和安金磊顯得很興奮,他們都來自河北的農村,到了這裏自然是如魚得水。李大哥告訴我們,這些堆肥的方法,過去的農村人都知道,而且中國農民一向是精耕細作,相比之下,帕翁示範所用的方法和工具,就略顯粗陋了。只是,現在大家用慣了農藥化肥,傳統的方法已不多用,結果難免是人懶地薄。聽著這些,我想起小時候背的節氣歌,不免覺得有些傷感。中國一向是農業大國,幾千年以來關於農時農方的記載多不勝數。回去後我翻了一些古籍,光是堆肥的方法就找到幾十種。而對於如何配合天時,如何分辨土壤美惡施肥,都有極為詳盡的論述——我們不遠千里跑到這裏來學習,卻不知自己家中就有無盡寶藏。
想著這些,耳中又聽見李大哥在講他承包的千畝荒山,他在荒山上種下的各樣的樹木以及他恢復傳統農耕的夢想。而安大哥則多次提到自己的棉花田、西瓜地,言語間流露出對於土地的深情。突然之間,我很想回去,回去多瞭解他們的世界,多看看國內的農村,多想想我自己的"南山之夢"。
帕翁和雲婉是夫妻,也是知己,他們在一起找到了自己的"南山",在喧囂的塵世中有了一方清淨之地。雖然不是在世外桃源,卻也有很大部分的生活不太受制於主流社會,正是"心遠地自偏"。因為不認同現行的教育,除了最大的兒子自己想上學外,他們沒有送其他的孩子去學校念書,而是留在家中親自教導,在田野之間學習自然的道理。想起國內的一些朋友,一方面極力抨擊僵化的主流教育,一方面又千方百計想將自己的子女送入所謂最好的學校,便不禁由衷地佩服帕翁夫婦言行一致。不理想的地方也是有的,帕翁說,他最希望的其實是做一個全職的農夫,成為一個隱士,同時也是一位導師。而現在的他,實在是太忙了,雖然想擺脫這種狀況,但是村民們來請他幫忙的時候又不忍拒絕,畢竟都是窮苦的老百姓啊。這些話,直到現在我還是記憶猶新。某些地方,我們是相似的,我自己也常在這樣的矛盾中徘徊。我在心中暗暗祝福帕翁,最終能在幫助別人和幫助自己之間找到平衡。
離開農場的時候,我看見一株長在樹上的蘭花燦爛地綻放著,黃色的花瓣一串串垂下來,帶著露水,格外清麗。雲婉說,這種蘭花花期很短,通常只有一兩天的時間,難得一見,這是在歡迎我們的到來。看著雲婉,我想起"空谷幽蘭"四個字。在中國的文化裏,蘭花一向是譬喻品行高潔的君子,而此刻,她正與我心目中帕翁夫婦的形象相互呼應。於是,這株美麗的蘭花就永遠定格在我的腦海中。後來,每當回想起這次泰國之行時,她就首先從記憶中脫穎而出,迎風綻放,成為生活在泰西山區中的帕翁與雲婉的象徵,也是對我的"南山之夢"一個真實而美好的詮釋。
"改變其實是一種回歸"
一到克倫族人的村子裏,我們就聽到了一個好消息:村民們在附近發現了十幾年不見的老虎腳印。克倫人相信老虎是山神的使者,它有時會下山來監察人們的活動,咬傷有不檢點行為的人,以示懲戒——沉寂了這麼久,監察使終於又回來看顧村人了!帕翁告訴我們,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那些進行有機耕種的村民。他們自己會很積極地保護森林,在山中巡邏,阻止人們伐木和盜獵。與現在相比,在最初的幾年裏,說服村裏人從常規耕種轉變成有機耕種是很困難的。大部分人是在一旁持觀望態度,他們認為有機耕種更辛苦,產量也不如使用化肥來得高。於是帕翁就鼓勵他的學生們在田裏辟出一個角落,用有機的方法種一些果樹和蔬菜進行實驗。所謂"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四五年以後,果樹結果時,他們的經濟收入就大大增加了,當然隨之增加的還有人們的信心。在市場方面,有機產品的價格要比普通產品高一些,也穩定一些,通常是由農民根據季節和實際的投入來制訂。這一類的市場,往往是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或由倡導公平貿易的民間團體來推動,不同于商家重利,他們更能考慮到農民的權利與權益。減少了中間商的環節,消費者也能用較低的價格買到放心菜。在生產規劃上,與常規種植相比,由於更少地依賴於大市場和大公司,農民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當親身體驗到這種種好處後,村裏便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到有機種植的行列中。
我們走訪的第一位農民進行有機耕種已經一年多了,是帕翁的第三代學生。他不是克倫人,而是從附近的村中搬遷到這裏的。他以前的家被政府無條件徵用來修建水庫,是泰國王室在當地一個綜合性示範項目的受害者。帕翁告訴我們,那個村子裏的人由於這個項目都喪失了土地,無法再生存下去。村民們出於對王室的尊敬,始終在安靜地等待政府的回音,希望能有一些補償。然而六、七年過去了,政府一方始終音信全無,而很多人也因此變成赤貧的邊緣農民。他們中的一些人便搬到這裏開荒種田,重建家園。
我們問這位農民為什麼願意轉變成有機耕種,他告訴我們,這樣他的收入更穩定,能讓他和家人生存下去,自己也不再受到農藥的傷害。而更重要的是,現在他們全家人都可以在一起工作。同時,因為有機種植要求多樣化,他們都能吃到更多種類的食物,生活品質也提高了。只是他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照顧菜地,沒辦法同時種稻米,現在他正想實驗看看能不能兼顧糧食和蔬菜。雖然辛苦,但是能夠一邊幹一邊學,學以致用,還是樂在其中的。
看著他的菜地,我想起帕翁說過,克倫人的這一片土地在法律上也是歸國家所有,只是實際上是由他們在使用。但是,就像那個泰王的專案,政府隨時都可以無條件徵用土地。如果有一天,真得發生這種情況,這些農民是不是又要流離失所呢?對於他們來說,土地的歸屬並非寫在蓋有鋼印的紙上,他們世代居住於此,他們的祖先埋葬在這裏,然而這一切或許突然間就會因為不知從何而來的一紙文書變成非法所有。而這些擺在政府官員桌上的文書中,永遠不會記下農民們對於安居樂業的夢想以及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感受到過的快樂。
聯想到國內愈演愈烈的圈地運動,修路、房地產、經濟開發區……鄉村的土地被以各種名義擠佔著,反映出我們集體無限膨脹的欲望。在這個以利為利的時代中,世界不同的角落裏上演的故事何其相似!
想著這些,我們又來到另一位農民的家,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小夥子帶我們來到他的地裏——一片在山上開墾的梯田。這裏本來是一片荒山,三年前,他成為帕翁的第二代學生,受益于帕翁帶進來的項目,他將這裏開墾出來,進行有機耕種。他告訴我們,經過三年的實踐,他已經很相信有機生產的信念,常規農業是種越多,賺越多,而有機農業是種得越多樣化,賺越多,像這一片田裏,就種了大約二十幾種不同的蔬菜。目前,他的菜更多是賣給大公司,而不是在本地的小型市場上銷售。因為為了建設這個農場他貸了很多款,要在幾年之內還清,公司每一次的收購量會比較大,他也能多賺一些錢。所以地裏生產什麼,有時候還是要看公司的要求。小夥子略帶靦腆地告訴我們,他的夢想是能有一個自己的大農場。
離開的時候,我看到田裏一棵大樹上掛著一串美麗的飾物,在一片青翠中格外醒目。我問他這裏面是否有什麼含義,他說,這些是用來紀念他的祖先的,逝者已矣,而他們還在祖先的蔭庇下繼續生活在這裏。
最後,我們見到了帕翁的第一代學生——有機農民合作社的主席昆。合作社是村裏進行有機種植的農民自己組織起來的,他們覺得一個人力量很小,在一起就可以面對更多更複雜的事情。昆進行有機種植已經五年了,以前他在曼谷打過工,也在不同的村子間搬遷過,尋找合適的土地,但始終都受到大市場的控制,負債累累。而現在,除了我們所看到的地以外,他又開闢了一塊新田,建了新的房子,同時他的健康和耕作環境也有了很大改善。
昆是由大家在會上選舉出來的,他的工作主要是協調管理村民的一些事務,並進行農業技術指導。他強調自己只是一個服務者,而不是什麼負責人,實際上,很多事是由大家一起來決定的。或許是由於泰國人大部分信仰佛教的緣故,不論是昆還是後來我所接觸的一些農民領袖,都給人一種非常謙和的感覺,讓人感到他們更願意做的是服務,而非領導。
昆強調,合作社在接受新成員時通常很謹慎。因為他們覺得社員的理念相近非常重要,不能夠只是看到經濟上的利益便來參加,而忽略掉其他方面。社員們在整個生產的流程中都會一起分工合作:種地、收割、包裝、運輸,共同面對市場。大家會經常在一起聚會,除了討論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分析市場的狀況以外,他們也會互相分享經驗,交流對於生活的看法。比如,一個家庭更重視什麼——賺更多的錢,還是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相聚。
昆還告訴我們,泰國的農民對大自然一向是很尊重的。在他們的傳統中有一系列的儀式向大地表達感謝及道歉。特別是作為稻米之國,米神在他們的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而傳統的生產方式改變以後,人們對於自然的態度跟以前已經不同。現在,他們又轉變回來,雖然很多東西難以再現,但至少能夠和以前一樣一家人在一起,自給自足。
先秦時有一首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今天的人注解說,最後一句是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百姓對於君王的不滿與輕視——"他們何曾幫助過我!"。以前並不覺得這注解有什麼不妥,而今日重讀,才明白其謬大矣。如果將"帝力"泛解為所有外界強勢的力量,那麼不被這些力量所打擾,甚至感覺不到這些力量的存在,人們只是順應天地間的規律生活,守本務實,心無外慕,這豈不就是老百姓最安然無懼的生活?
掌握更多資源的人往往有更多狂熱的妄想,比如以為科技能夠解決一切問題,便有了各種違背自然規律的做法;比如追求絕對的致富,霸王硬上弓式的發展,用外界強烈的刺激來調動人無限的欲望,以此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而往往片時的繁榮卻只是如同一個人在虛陽外越的亢奮狀態,收斂不足,耗散有餘,如此,本來就薄弱的本底終有一天會被掏空,病入膏肓。長久以來,農民們被各種聲音左右著,先是七十年代的"綠色革命"告訴他們:"你們的小農生產方式是落後的,用我們的農藥、化肥和改良的種子吧,這前景一片光明"。而今,城裏的人到鄉村時卻問他們:"你們為什麼還使用農藥呢?你們不知道它污染環境、損害健康嗎?"同時,第二次"綠色革命"的浪潮又來勢洶湧,農民們又被告知:"用我們的轉基因種子吧,這是解決貧窮和饑餓的最好的出路"。另一邊,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說:"你們要致富,致富光榮,不致富是狗熊"。在土地上耕耘了千百年的人們無所適從了,各種"革命"切斷了他們與過去的聯繫,如同沒有根系的浮萍,在水上飄搖。而在這裏,泰國西部山區的一個小村落中,我卻看到農民們在這樣的夾縫中努力著,尋找自己的位置,重拾先人的智慧——被攪亂的世界漸漸澄淨。
此時,我想起帕翁引用過的一句話:"自然農法要改變的不是土地,而是人。不是人的耕作技術,而是他的生存態度。改變其實是一種回歸"。
"農場的生命和我的意志力緊緊相聯"
"第一是不耕田。因為人不去耕耘大地,自然也會耕耘她,而且地力還會逐年增強。"
"第二是不施肥。如果人類進行拙劣的耕作,採用掠奪性農作方法,土地就會變得貧瘠,成為需要肥料的土壤。而在自然的土壤上,動植物的生活環境越活躍,土壤本身也就越肥沃。"
"第三是不使用農藥。大自然通常是保持完全平衡的,不會發生需要人類非使用農藥不可的病蟲害。只有在進行了不自然的耕作、施肥和培養出了病體作物時,"病蟲害"才會出現來幫助恢復自然的平衡。"
"第四是不除草。草為自身的繁衍而生長。雜草之所以也生長,說明它在自然中發揮著某種作用。同一種草不會永久地佔據一塊土地,到時必將發生更替。草的問題由草兒們自己來解決,這應該作為一項原則……"
這是自然農法之父——日本的福岡正信老人所提出的自然農法[3]四大原則。
福岡老人年輕的時候是一家實驗農場的農業技術員,曾經一度醉心於各種農業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中。然而後來的一場大病卻使他完全改變了看法,開始質疑一切源于"人智、人為"的現代技術。在病中,類似於頓悟的體驗讓福岡堅信"人智、人為皆是無用之物",只有"順其自然、不戰而勝"的農作方式才是農業發展的正途,而老子"自然無為"的思想和釋迦牟尼關於"一切皆空"的教誨便成為這一信念的基石。病癒後,福岡辭去工作,開始潛心實踐"儘量什麼也不做"的自然農法,從此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幾十年過去了,年輕的福岡變成了隱居山中的長者。在世人眼中他曾是不可理喻的瘋子,如今人們卻從四面八方慕名而來,到他這裏尋求智慧。而福岡老人所倡導的自然農法也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在泰國考察期間,我就曾經不止一次地聽人談起過自然農法,在這個虔信佛教的國度裏,它似乎更能貼近人們的心靈。在行程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去拜訪了位於曼谷近郊的東棠農場——一個立意要實踐自然農耕的地方。
東棠農場占地約有100畝,半天的訪談中,我們沒有太多時間參觀農場的全貌,如今只記得其間幾座雅致的建築以及一大片綠油油的水稻田。倒是與農場負責人狄塞先生的一番懇談讓人印象深刻,至今難以忘懷。
狄塞大約三、四十歲的樣子,接待我們的時候卷著褲腿,光著腳板,穿著一身沾滿泥土的舊衣衫,遠遠看去,倒像個地道的農民。近了,卻發現他瘦長的臉上原有一股濃濃的書卷氣。
狄塞告訴我們,最初是幾個推廣有機耕作的朋友支持他建立起這個農場。其中的一個人推薦他看福岡老人寫的《一根稻草的革命》,受到這本書的影響,他決定要身體力行來實踐自然農法。狄塞說:"現在很多民間團體都想要改變人們的價值觀,讓城市人重新與自然建立聯繫,但是他們自己卻不能真正實踐。我覺得脫離土地來說話,這樣是不可取的"。
不同於靠政府投入的示範性農場,狄塞和他的朋友們不願過分強調經濟方面的利益,變成徒具形式的"有機"。他們希望農場能夠真正體現自然農法的內涵,並能發揮教育的功能,影響更多的人。狄塞自己會寫一些文章,放在農場定期的通訊中。通訊是他們與外界溝通的橋樑,會包括農場當前的狀況、自身理念的宣傳以及一些生活化的指導。農場還會開展一些培訓活動,參加者是那些真正對自然農耕有興趣並願意長期投入其中的年輕人。在農場中他們可以學習如何遵循自然本身的規律,使其間的各樣事物各安其位、相互結合、循環往復。比如雜草可以做為雞鴨的飼料,反過來雞鴨可以幫助除草吃蟲,而它們的糞便又可用來肥田等等。"當然,重要的不僅僅是提供技術,而是讓人們瞭解這種自然迴圈的理念。不同的地方,具體的實施方法是不一樣的。"狄塞強調說。
農場最初的投入是依靠基金會的資金支援,此後的運轉和工作人員80%的工資則需要靠自身來解決。為了能夠自給自足、自力更生,農場要提供日常所需的各種食物:大米、蔬菜、水果、雞鴨……除去供給自己的工作人員外,剩餘的還要賣給消費者,換取現金。狄塞和同事們不想把農產品賣到超市里或是其他倡導公平貿易的民間團體中,而是建立了一個"社區支持農業"[4]的網路。因為他們看重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直接的溝通,希望彼此之間不僅僅是冷冰冰的買賣關係,而是有一個相互瞭解和信任的基礎。
在北京的時候,我和同行的朋友們也曾經探討過"社區支援農業"的概念,因此我們請狄塞多給我們講講他的經驗。
狄塞:"社區支援農業"的項目我們已經進行了三年。最開始的消費者都是周圍的朋友,慢慢的這些朋友又會介紹他們認識的人加入進來,成為會員。那時候我們想得很簡單,就是先規劃好農場的規模,看看能供應給多少人,然後計算運營一年的成本(包括工作人員的工資在內),最後訂出農產品的價格。會員們要先預付一年的錢,我們則是每兩周到曼谷送一次菜。但是當我們實際做起來的時候卻發現其中困難重重。首先是推廣這種方式很難: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更喜歡去外面吃飯,而在家做飯的人也往往是去超市或大市場買菜,不太適應共同購買的方式。此外,關心健康食品的消費者一般住得比較分散,彼此之間沒有太多互助合作,這就給運送農產品到每家每戶增加了困難。另一方面,我們計算成本的方式也有問題,三年來一直虧損。後來我們提高了價格,有的消費者就覺得難以接受。這個農場運營的成本確實比較高,很大一部分要用於支付工作人員的工資。所以我們也與消費者溝通,勸他們不要去比較價格,因為每個農場的情況都是不一樣的,我們確實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制定。
問:這樣的話消費者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狄塞:有一些人很開心,他們認同我們的理念,對於價格上漲和由於自然因素引起的菜量不足也能理解。有一些人就覺得問題太多,不能接受。這其中有我們運營的問題,比如在管理生產方面,效率太低,人手也不夠。在推動消費者的參與上也不太成功,他們沒有參與耕作、流通和管理,所以相互間的理解不是很充分。大家似乎更多是出於感情和個人關係來支援我們。三年以來,有人加入,也有人離開。現在這個項目已經停止了,停止之前有十五家是我們的穩定顧客,我們相信如果這個項目再重新開始的話,他們還會回來。
問:為什麼現在會停止呢?
狄塞:我們是個很小的組織,只有三、四個人,像個家庭一樣。工作人員不是親人就是朋友,沒有從外面招聘過。我們想兼顧生態環境、自身生存以及社會服務三個方面,三者要達到一個平衡。家庭農場的好處就是比較容易維持這個平衡,不會像其他很多地方,太注重於個人利益的獲取。不利的地方就是人手太少,對於我們來說,現在的規模太大了,不得不停一段時間,在人員上進行一些調整。其實單純維持一個農場,三個人也沒有太大的問題,但作為一個民間組織,我們還要擔負很多額外的工作。我一個人要種地,要寫東西,要計算成本,同時還要負責對外聯絡、運送農產品……根本沒有時間休息,壓力很大,常常覺得疲憊。現在我們也在思考是否需要採用商業運作方法,這樣可以聘請一些工人,也能供應更多的人吃上有機食品。
我忍不住問他:"您當初為什麼要來到這裏呢?不是想要找到一塊清淨之地,來實踐自然農法嗎?但現在反而給自己找了這麼多的麻煩,出現這麼多的問題,這豈不是與初衷背道而馳?"
狄塞笑了笑,說這個問題正中要害,他自己也在思考。"我在大學的時候是讀新聞傳播的,做過老師,也在曼谷做過新聞工作,但是它們都不太適合我。我是一個佛教徒,更喜歡接觸一些能夠對心靈成長有幫助的事物,比如和自然打交道,在土地上耕耘。所以,我就辭去了在曼谷的工作,進入到民間團體中。一段時間以後才發覺我不能只在辦公室中工作,還是要待在農場上。我是那種思考型的人,常常處於很緊張的狀態,所以需要體力勞動,在自然中得到放鬆。我也想過去做一個和尚,但是現實的情況不太允許,所以還是農耕最適合。"
"其實一直以來,我更想做的是種地,而不是整個團體的工作。'社區支持農業'的專案停下來以後,又發生了很多事情。先是禽流感的到來,我們的雞鴨都沒有了。然後是跟綠網[5]的合作,他們不願意再支持我們。另外,我們的土地是租用的,主人由於負債要賣出一部分做抵償,這樣我們的地也有了問題。正所謂禍不單行,前天晚上我們種植稻米用的機器也被人偷走了。"
"有一段時間,我很想離開這裏,在鄉下買一塊自己的田,做一個全職的農民,不再去想其他的事情。但是,我現在又覺得農場的狀況和我自己的狀態有關,農場的生命和我的意志力緊緊相聯,如果我現在一走了之,她也會漸漸衰敗下去。我無法解釋這個感覺,但它就是這樣。"
望著狄塞極為瘦削的臉,我的思緒也漸漸亂了起來。福岡老人說:"農業是為侍奉神、接近神而存在的,它的本質也就在此。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神便是自然,而自然就是神"。但是在現實中,卻很少有人視自然的饋贈為神聖的給予,少數幾個人的努力就顯得格外艱難。
我想起帕翁,他也說過,自己想做一個全職的農民,少管一些事情,多花一些時間在土地上。但哪里是與世無爭的田園呢?短短的一天裏,我們看到的是他們恬靜安詳的生活,看不到的卻是他們十幾年的奮鬥過程,我們看不到他們怎樣和伐木公司周旋,怎樣為克倫人奔走呼籲,怎樣為他們並不樂觀的明天憂心忡忡。或許帕翁和狄塞應該遵從自己內心真正的感受,去做一個純粹的農民?而我自己呢?在未來,我的選擇是在一片真實的土地上實踐自己的夢想,還是在民間團體中做著各種教育推動的工作?兩者之間應該如何平衡?普通的農民很少會有這樣的矛盾和煎熬。對於世代務農的村民來說,他們與土地似乎是彼此的一部分,沒有太多道理講得出來。普通農民不能像帕翁一樣在山中還能無線上網,也不會有東棠那種規模的農場,那樣大的投入。對於帕翁和狄塞,土地更多是象徵著心靈的歸宿。或許成為一個全職的農民,始終只是他們心中一個美好的嚮往。
我敬佩帕翁與狄塞的實踐精神,他們的坦誠以告也讓我漸漸看到自己在將來的工作中可能要面對的挑戰。我無法揣度狄塞是用怎樣的心情來講述他的故事,一個人的舍與得往往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的,多年的經歷被壓縮在短短的一段話中,遺失了細節的描述無法展現出完整的畫面。
在狄塞的心中,自然農法的真意又是什麼呢?福岡老人在《一根稻草的革命》中寫到:"自然農法是一條永遠無法徹底修成的路。自然不是靠人智、人為可以探索出的,也不是靠人智、人為可以創造的。我的享受就在於以舒暢的心情建設我心目中夢幻般的自然農園。現在,我躲在山中的小房裏,不接受任何人的訪問。我的農園從今年起也不再對外開放。這樣做都是因為我要珍惜所剩無幾的人生……總而言之,要加入到自然裏、與神同在,就不應借助他人的力量,也不應去幫助他人。"
無門的大道 空無一人
天靜寂無聲 地喧騰鬧人
是誰掀起了巨浪狂風
忽左忽右 防守進攻
什麼是好 什麼是壞
一把扇子兩面搧出的風
送來的都是愜意的涼風
在無人的田園裏搭起臨時的草庵
今日一天恰似人生百年
蘿蔔、油菜花、盛開的鮮花
二零零零年月色朦朧時
不顧一切穿過這個世界、那個世界
漂泊不定 遊蕩在旅途中
不再思慮結果的如何
在我們眼中看來,東棠農場的經營多少是有些失敗的。但是誰又知道,在我們離去的那天,那個靜謐無人的夜晚,狄塞不是在這樣的心境中獨享著他的幸福呢?
"種出一個完整的人"
在國內的時候,一提起泰國,就總是聯想起細細長長的泰國香米。想像中,泰國仍然保留著傳統的耕作方式,而泰國人應該是每天都很幸福地吃著"噴香"、"可口"、"綠色無污染"的香米。及至親臨其境,在他們的餐館中吃了幾次飯才恍然大悟:原來普通的泰國人和普通的中國人一樣,都是吃普通大白米的。同樣,在國內的時候,我怎麼也想不到以"稻米之國"著稱的泰國竟然也要從中國進口稻米。而且,泰國人普遍認為中國米"噴香"、"可口"、"綠色無污染",比起本國用農藥化肥種出的大米要安全多了。
在泰國北部的清邁,當可持續農耕協會的負責人告訴我們這些情況時,我突然之間有一種感覺:我們所有人都被這種跨國貿易的遊戲給涮了。記得同行的寶熙老師曾經講過,在全球化的食物系統裏往往會發生這樣的事情:1996年英國進口超過114,000噸的牛奶,但同時出口119,000噸牛奶;美國人吃丹麥曲奇,丹麥人則吃美國曲奇。隨之而來的是讓人眼花繚亂的廣告,刺激著消費者的購買欲望,我們往往是不加辨別就接受了這些訊息,乖乖掏出自己的腰包。而為了使這些進行長途旅行的食品不變質所添加的大量防腐劑、蠟、真菌抑止劑等等化學品,則被巧妙的掩蓋了。更不必說進口蔬果因為被長時間放置而導致養分大量流失的問題。此外,這些不必要的交換引起的不必要的長途運送所造成的難以估量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也是進入不到我們這些普通人的視線中的。究竟誰在其中真正獲益呢?
泰國國家的財富一直都來自於農村,國家靠出口糧食賺取了大量外匯。而諷刺的是,在這裏最貧困的也是農民,他們的財富一經生產出來就被奪去了。為什麼呢?
協會的負責人告訴我們,泰國政府和幾家大的跨國貿易公司始終不餘遺力地引導和鼓勵泰國農民進行單一品種的大面積種植,。他們為這種轉型的農民提供各種配套支援,給農民提供貸款,或是在最開始的時候低價賣給農民種子、化肥,同時高價收購農產品,甚至給農民高額補貼,鼓勵他們只種植供出口的農作物。
但當轉型的農民開始變得越來越習慣並且依靠這個系統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所有的優惠政策就都消失了。種子、化肥變得很貴,而且必須每年都買——從公司買來的高產作物是沒法自己留種的,同時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卻變得越來越低。至於貸款,根據規則,在收穫的季節裏農民要賣掉大米來還債,面對急著還債的農民,中間商又可以乘機再壓壓價格。賣掉大米換了錢,農民再去買自己所需的口糧。問題是,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很低,賣出的價格則要高出幾倍甚至幾十倍,沒有人知道這些價格是怎麼制訂的,只有中間商掌握著其中的玄機。而這其中的一出一進,總讓農民覺得心裏不是滋味,但又說不出所以然,手中的現金是多了,可是消失的卻更快。據說這些中間商很多是中國人,我們聽了不覺有些赧然。
二零零三年十月,中國和泰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規定中國可以向泰國出口160種產品,其中只有5種要抽稅。也就是說其他155種可以以很低的價格進入。以大米而言,低價的中國米進入泰國,衝擊著本地市場,原本10個泰銖[6]1公斤的大米,現在5個泰銖就可以買到。市場的這種變化對一些單一種植大米的農民產生了毀滅性的衝擊,因為他們早已失去了自給自足的能力,除了稻米沒有其他的生活來源。稻米價格的下跌導致他們背上越來越沉重的債務,最終不得不出賣土地,到城市裏去打工。而城市的夢也很快破滅了,當這些人想重返故土時,已經沒有土地能再接納他們。大片土地已被大地主所佔有,而這些大地主通常是來自曼谷或其他國家的公司和集團。
一些民間團體指出政府不應大力鼓吹自由貿易,因為自由貿易沒有公平性可言,在資源、權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只能使強者更強,弱者更弱。農民所嚮往的生活狀況其實是能自給自足,自己團結起來面對生活,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持續下去,並得到幸福與和平。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往往被政府懷疑是有分離主義的傾向。
為了幫助在自由貿易中受害的窮苦農民,可持續農耕協會鼓勵農民進行可持續耕作,重新恢復自給自足的能力。同時幫助農民自己組織起來,和消費者共同發展本地認證、本地市場和本地教育。這樣,在本地一個小範圍內運作,通過消費者的參與,就有可能建立對農民和普通消費者都更為公平合理的市場。為了使農民能夠逐漸減少債務,協會也鼓勵農民成立自己的社區公共基金,使他們不用再向銀行貸款,不必再去償付較高的利息。
在清邁,一些民間團體嘗試通過三種具體的方式來推動公平貿易:建立有機產品銷售中心、流動市場和社區支援農業的網路。銷售中心由農民和消費者一起以合作社的形式成立,並共同選舉管理委員會進行管理。農民們將新鮮的農產品或是加工品賣到銷售中心,再由中心通過批發及零售的方式賣出。不過據說由於中間隔了一層管理委員會,農民沒有直接面對消費者,不能瞭解市場的情況,所以合作過程有些問題,其中也產生了一些信任危機,不是特別成功。而天性喜歡自由的泰國人也不太適應社區支持農業的形式,因此三種方式中比較成功的是流動市場,也就是我們在國內常見的菜市場。農民們更喜歡自己到市場中直接把農產品賣給消費者,這會讓他們覺得心中更踏實,也更有歸屬感。
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其實是清邁的民間團體、農民們和有心的消費者共同努力了十幾年的成果。而這些成果就反映在人們日復一日的生活中:每天附近的居民提著籃子逛菜市場,便能買到更健康的食品;很多邊緣農民也因此恢復了正常安寧的生活,並且漸漸成長起來,比起以前能夠更好的保護自己。而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也多了一些思考——對於自然,對於現代化、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對於習以為常的消費方式……
可持續農耕協會的負責人告訴我們,在整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最困難的也是教育。因為政府和大公司並不是為了可持續發展來推動有機農業,而是為了出口;他們對農民進行技術上的培訓,卻並不鼓勵農民去思考。而這類所謂的有機耕作也大部分是進行單一種植,完全不符合真正有機標準中關於多樣性的規定。對於農民來說,重要的是真正瞭解貧困背後的原因,看清楚自己所處的環境。這個過程並不容易。不過,一旦農民有了自己的組織,他們就很難再被公司拉走。此外,政府和民間團體在宣傳教育上用著相同的辭彙,有著相同的口號,甚至在實際操作上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事實上卻表達著不同的內涵。有人擔心,這樣會引起普通民眾概念上的混淆。
面對這些問題,他們無法安于現有的成就,深感任重而道遠。最後我們結束此次拜訪時,協會的負責人仍是以福岡老人的話做結語:"……裏面的靈魂才是最重要的。農業最終的目標不是種出作物,而是種出一個完整的人"。
"貴族學校"裏的菜農
在清邁,我們參觀了兩個有機菜市場,受到不少啟發。其中一個在居民區附近,每週開三天,都是由農民們自己來管理。一大早,村子裏的女人們就會帶上自己頭天收割下來的農產品,一起坐車來到這裏。之所以都是婦女來,是因為大家覺得婦女更容易跟人溝通,能夠更好地瞭解顧客的需要。市場不大,卻乾淨整潔,大家都穿著藍色或綠色的制服,親切地微笑著。藍色說明這家人沒有經過有機認證,但是農民協會可以證明他們確實是在用有機的方式生產。綠色則表示已經認證過了。制服上畫的是本地認證的標誌:一個泰國傳統樣式的屋簷下並列著兩片本地野生植物的葉片,整個看起來像是一個綠色的笑臉。屋簷象徵著幸福的家庭,而這種本地野生植物的葉片據說很有營養。整個標誌可以用三個辭彙來概括:本地化、幸福、健康。農民們覺得穿上整齊的衣服,會給別人留下好印象,也會讓大家更信任這個市場。
我們在市場中逛來逛去,似乎每個攤位上都有些新奇的東西——從來沒見過的水果、蔬菜,農民們自製的茶葉,現場製作的包在芭蕉葉片中的傳統小點心……正好,在市場外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賣常規種植蔬菜的小攤,我們比較了一下價錢,發現兩邊基本持平,大部分有機蔬菜並不昂貴。省略了中間的流通環節,購買有機食品也不一定只是有錢人的消費。我們還發現,同一種東西,在有機菜市場中的價格都是一樣的。原來農民們會定期開會,在會上協調誰賣什麼,賣多少錢,同樣的東西不能有價格上的差異,以免造成惡性競爭。
市場外面有一排宣傳欄,內容都是介紹有機的概念、生產過程和本地認證系統的。和我們國內不同,泰國的有機認證不是由政府來做,而是靠民間團體來推動,而且全國性的認證系統和地區性的本地認證系統並行,有更多的靈活性。倡導本地認證的人認為全國性的認證花費太多,給小農戶造成的負擔比較重,而且每個地區都有自己不同的情況,不應一概而論。認證說到底,是要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一種信任,所以也不應該讓消費者僅僅看到一個標誌,更重要的還是相互之間的溝通,認證規則也應該是由農民和消費者一起來制定,而這一點在小範圍內更容易做到。
另外一個市場則設在一所教會學校中。每個禮拜三的下午,農民們就會來到學校裏,等待下課後蜂擁而至的師生們。我們先去拜訪了學校的老師,想不到一進去就受到了很正式的接待。在他們豪華的會客大廳裏,我們吃著精美的點心,聽校長為我們介紹學校的歷史和現狀:七千多名學生、三百多位老師、十二座大型建築物、各種現代化的教學設備、接待過泰國王室的視察……最後,當所有的介紹結束時,我已經在冰冷的空調風中凍得瑟瑟發抖,開始懷念起泰國傳統的居室——竹子搭成的高腳屋,坐在裏面怡人的涼風習習吹來,不燥不寒。
忍著哆嗦,我問校長為什麼會提供場地給農民們賣菜。校長說開始是因為學校開展的環境教育活動在省裏得了獎,所以有機農民合作社找到他們商量在學校建立流動市場的事情。學校方面也覺得自己有義務推廣有機生活和進行公眾健康方面的教育,就接受了這個提議,在校內專門辟除了一片地方。我們又問她對學生在有機生活方面的教育都包括哪些內容,是否有一些實踐的活動和與農民交流的機會。校長說,學校的教育只是定位在食品安全上,會通過學生協會做一些宣傳教育。學校能夠提供場地給農民們就已經盡到了責任,沒有再專門安排其他活動。
接下來是學生代表的發言,一個小姑娘拿著稿紙向我們做"彙報"。我們很驚訝地聽到她說,學生協會有時會在有機菜市場中買一些菜,偷偷送去化驗,而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發現農民們有作弊行為。這就是所謂的有機生活教育!
最後,我們終於來到市場上,此時學生們已經放學,迫不急待地跑到這裏來了。看得出來,很多孩子喜歡這個地方。農民們也和我們去參觀的前一個市場一樣,穿著綠色或藍色的制服,把自己的攤位弄得清清爽爽。農民協會的主席也在其中賣著自家的菜,這個一臉慈祥的中年女人看起來只不過是所有賣菜婦女中的普通一員。我們坐在市場一角,同她攀談起來。我問她會不會覺得用有機的方式種田太辛苦,不使用農藥的話,蟲子的問題是不是很難解決。她笑笑告訴我說,有機耕種是很累的,但是比起常規種植有太多的好處。至於蟲子,它們要生存當然也要吃菜啊,它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再問她如果農產品能就近賣掉的話,是不是就不走這麼遠到這裏來了?她連連擺手說,不會的,來這裏看到這麼多孩子心裏就覺得很高興,這裏很好玩。我們都笑了起來,剛才在會客大廳裏的不快一掃而光。
至今,每當想起這位快樂的菜農,我都會忍不住地微笑起來,心裏覺得很感動。我不知道貴族學校裏的師生中有沒有人曾經好好地注視過她們,我不知道大費周章把菜偷偷送去化驗的孩子們除了冷冰冰的檢測以外,是否也願意多用心去瞭解一下農民們的生活、種地的艱辛和他們的情感。孩子們長大以後會關心什麼呢?有機教育真正的內涵應該是什麼呢?記得同行的安金磊曾經說過,作為農民,他很反感"有機"這個辭彙。當這兩個字漸漸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用語時,也就漸漸失去了靈魂。城市裏的有錢人可以開著車到超市中去購買"有機食品",或是到高檔酒店中消費"有機菜",他們關心的只是一己的健康。同時,他們過度消耗資源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卻讓整個世界更不健康。而農村的種種疾病正是與這種城市的不健康息息相關,城市人對於農民的冷漠則加速了病情的惡化……
最後,在清邁,我們拜訪了美達村中一個很成熟的農民協會。在那裏,我們又看到了幾天來不斷從農民身上看到過的那種自信與快樂。從協會幾個負責人的敍述中我們深深感受到農民自己組織起來,相互合作面對生活是多麼重要。然而,這種感受更多來自於身臨其境的體驗,在匆忙的旅程中,我們沒能真正深入去瞭解這個美麗的村落,儘管這裏應是有著很多故事的地方。
[注釋]
[1] 石戶之農、荷蓧丈人都是中國古代的隱士。傳說舜曾想把帝位讓給石戶之農,但是石戶之農拒絕了他,攜妻兒隱居到海上。荷蓧丈人的故事則來自於《論語》,這位用手杖擔著竹器的老人曾經對孔子的學生子路說過這樣的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2]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節,二十四節氣共七十二候,每一候有一種相應的物候現象,叫候應,以人們能直接觀察到的自然現象來反映天地間陰陽寒暑的變化。如驚蟄三候的候應為"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周髀算經》中說"二至者寒暑之極,二分者陰陽之和,四立者生長收藏之始,是為八節,節三氣,三而八是故二十四。"
[3] 關於自然農法的介紹均參考福岡正信老人的著作《一根稻草的革命》,北京大學出版社曾於1994年出版過中文譯本。
[4] "社區支持農業"的概念於20世紀70年代起源於瑞士,並在日本得到最初的發展。當時的消費者為了尋找安全的食物,與那些希望建立穩定客源的農民攜手合作,建立經濟合作關係。現在,"社區支援農業"的理念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傳播,它也從最初的共同購買、合作經濟延伸出更多的內涵。從字義上看,"社區支持農業"指社區的每個人對農場運作作出承諾,讓農場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為該社區的農場,讓農民與消費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擔糧食生產的風險和分享利益。
[5] 綠網是泰國一個著名的倡導公平貿易的民間團體,在下面有專門的章節進行論述。
[6] 4泰銖約合1元人民幣。
 帕擁在他的農莊裡為我們講解他們的工作 |
 注意看屋檐下——自制的雨水收集器 |
 雨水通到這口紅肚子的大缸裡 |
 農場裡傳統泰式風格的小亭子 |
 帕擁給我們看他制作的液態肥 |
 廚餘堆肥區 |
 落葉堆肥 |
 克倫人的村莊裡多樣化種植 |
 山坡上梯田裡的多樣化種植 |
 還在靠借貸種梯田的小伙子,他的夢想是有自己的可持續農場 |
 能起到保水和控制溫度的覆蓋技術 |
 潔青為我們做翻譯,她手指向的就是村裡農民合作社主席 |
 與協會負責人互贈禮物 |
||
 在可持續農耕協會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流動市場 |
 身著統一服裝的農民合作社成員,除了賣農產品,還有她們自制的傳統小吃哦 |
 每個攤位前都掛著清邁本地認證標志——像征健康、幸福的笑臉 |
 流動市場前關有機農業介紹的宣傳牌 |
 一所學校裡的流動市場——每周三下午的集會 |
 與農民合作社婦女領導座談——好像鄰家慈祥的大嬸 |
 小店東西真不少 有機生活沒煩惱 |
 看看一臉燦爛笑容的璇璇,手裡拿的是當地農民用自己種的有機棉花手工制作的布袋 |
|
 與美達村可持續社區農業合作社座談 |
 美達的牛 |
 合作社辦公室 |
 做宣傳教育用的圖:關於農田多樣化種植的規劃——都是農民自己做的 |
 做宣傳教育用的圖:關於食物的說明 |
|
 在農場的亭子裡,農場負責人為我們講解農場社區支持農業的運作 |
 負責人像農民,像知識分子,又像個在土地上修行的僧人 |
 農場稻田 |
 稻田旁的水塘,典型的鴨稻共作,鴨子每天在這裡游水(當然水塘的作用不僅是給鴨子提供樂趣:) |
 農場裡的合影 |
|
 綠網總部門前——氣派不凡 |
 綠網辦公室,充滿了各種文件資料、宣傳畫 |
 綠網的有機商店——東西價格不菲,不過其中很大部分是返給農民的,是一種公平貿易 |
 有機休閑食品——像商家運作那樣專業是綠網運作的原則之一 |
 與綠網負責人座談 |
 後台生鮮食品加工 |
 說英語的CUSO負責人竟然是佛教徒,說起話來也就處處禪機 |
 泰國錢?——不是,是社區貨幣 |
 社區貨幣的反面,充滿協作精神的圖案 |
 別看下面看上面,傳統的泰式生態建築,屋頂是用樹葉做的 |
 雲婉和帕擁的孩子們。最小的那個在分別時說:"你們快走吧,別再佔著我媽媽啦" |
 中間坐的就是陪了我們一路的雲婉 |
 小橋 美女 人家 |
 分別的時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