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春泥[1]
插画 ▏ 全海燕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你会用它来种什麽呢?
当我翻阅社区伙伴推荐的《沙乡年鉴》[2], 我仿佛看到奥尔多·利奥波德和狗走在多年生活的沙乡农场,怀着爱注视着土地上的生灵自在生息,为他们在“进步”洪流中的消逝而悲叹丶疾呼。他激励我,回到源头重新理解“土地”,这串联起我生命不同阶段的体验,感到内在力量的整合,愿更扎实地为土地自然做点什麽。
聆听:大地上消逝的灵,我们灵魂的挽歌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座山,你印像中最深刻的那座山是什麽呢?”

2015年我参加种籽心田和燕山学堂[3]合办的首届“种籽行者计划”[4],在翻越一座大山前,清水老师问我们。我想起家乡的山,那里自然纯净丶亲情厚重。河水丶稻田丶青山,清晨淡淡的雾萦绕竹林,黄昏爷爷顶着晾晒菜干的竹篾回家。有次家乡发大水,他翻进窗户,抢背出年迈的太奶奶。当我大病回乡,家人带我上山,爸爸找笋一找一个准,从小带我的奶奶已经满头白发依然身手敏捷,查看地形告诉我们有野猪,我感到山的温情与神秘威严。
所以,当我看到《沙乡年鉴》,山和熊的故事,我特别难受。
艾斯卡迪拉山,有一个神秘而确凿的存在,那就是大灰熊,它本是当地人们生活闲谈不可缺少的话题。每年春天,它会从冬眠中醒来,下山吃掉一头牛,然後爬回洞穴,靠着土拨鼠丶蹄兔丶浆果和树根,悠闲地度过夏天。然而当“进步”之风刮来,人们开始关注驾车横穿美国大陆丶妇女投票权,甚至有老人好奇电话线能否送来熏肉,最後来了一位捕兽员,用尽各种办法杀死了熊,它甚至无法留下一张像样的皮。
从创世之初,岁月不断在这座古老的山脉留下印记:庄严的外表丶较小的动植物群落和一只大灰熊。[5]
而熊,死了。没有熊的艾斯卡迪拉山,也“死”了,尽管它依然威严耸立。
有多少大地上流动的灵正在逝去,谁来定义“进步”,谁在发展“权利”的同时负责?
威斯康星州野生火鸡丶赤鹿被灭绝,最後一群旅鸽变成馅饼。田鼠啃光了许多年轻果园里的果树皮。一头愤怒的奶牛引发了1871年的大火。过度种植小麦的土地失去肥力。麦迪逊的春花比往年足足晚了十三天。无雪的冬天,可怜的苹果树纷纷被冻死。叶蜂流行病摧毁好几百万美加落叶松。沼泽的水被抽干开辟农田,却成了废墟……
我想起简浩炀老师[6]问,“你们可曾亲吻过大地?”如果我们感受过她母亲般的胸怀,体会飞鸟野花树木自在繁衍生息之美和独特的生命故事,正如我们的兄弟姐妹与邻居,我们是否会对他们的逝去,无动於衷?
我们以为保护的是熊,其实是整座山和它的历史。
处在生物金字塔顶端的人类,无视和掠夺支撑着我们的土地的自然生命,死去的也是我们的灵魂。
反省:重建人与人丶人与土地的连接
当我听到地铁边卖水果的父亲训斥儿子“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像我一样”,格外心酸。我们怎样去看待“教育”对於时代的意义呢?正如利奥波德提醒我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群分崩离析的危机,同样也发生在人与土地构成的群落。在城乡差距丶工农业剪刀差丶消费文明等影响下,农村人潮涌入城市,而那里却并非梦想中的世界。土地丶空气丶水丶光电处处污染,我们失落的不仅是土地,更是它所承载的文化自信丶劳动者的尊严丶人与人的信任。乡土的消逝亦是文化自信的消逝。
经济需要有道德与美学的前提。我们的一切,如美好家园丶更好的教育,都要有利可图吗?经济的力量,应该是驱动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与我们这些前提和谐相处,更可持续地生活。
我也曾每天在流水线前站十多个小时,因手笨完不成既定产量被训而哭;当成为熟练工後,却在夜班时倚着机器感到“绝望”。工厂里有人说茫茫人海自己像小草一样被淹没,有人整晚加班天快亮时一松神被机器打到伤残;单打独斗维权困难重重……
我始终记得,一个工友姐妹和我说,她想回家,她想回家养蜂。
那一瞬间,惊醒了我,我看到长期被轻视丶需要被拯救的“乡土”的意义,也正是它,在城市金融危机工厂倒闭之时,拥抱大量失业回乡的人们。
半塔村是个打工人群聚集生活的流动社区,人与人彼此间的关系比较陌生,我们在“农民之子”[7]办起社区厨房,用“食物”连接土地丶分享生活,拉废砖运土砌花坛种蔬菜。在饭店当大厨的爸爸第一次发现儿子自己做饭原来这麽好吃!孩子妈妈教我们腌咸菜。山西小伙儿的臊子面是记忆中妈妈的味道。社区修自行车的大哥慷慨提供冰箱存放我们手作的健康冰棍。一起过“中秋节”,挂灯笼丶猜灯谜丶烤月饼丶拜月亮,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提着亲手做的灯笼走过平日嘈杂的街巷,流动的光,大人看到自己的童年,孩子追着我们跑……自然和社区是我们的教室,身边人是我们的老师,在奔波生计中点亮心灵的光,唤起对当下“美好”的追求,生活也有不依赖“钱”的更多可能,由我们彼此分担丶一起创造丶共享情意自然。
燕山怀抱长城之畔,我们在燕山学堂和志愿者丶孩子一起造“土”?!整地丶打木桩篱笆丶铺废纸皮丶捡树枝,放上长期积累的厨余,倒上木屑,一起为它们祝福,期待长出“新”土种蔬菜!孩子念念不忘,厨余的味道真是太酸爽了!在记忆中,已有一小块土壤播下了种籽,有惜福丶感恩丶互助丶坚持丶期盼……那是在亲近土地劳作中美好的品质。因为付出过,我也会时常照顾这小块地,当我看见木屑堆上长出几颗晶莹剔透的菌菇时,我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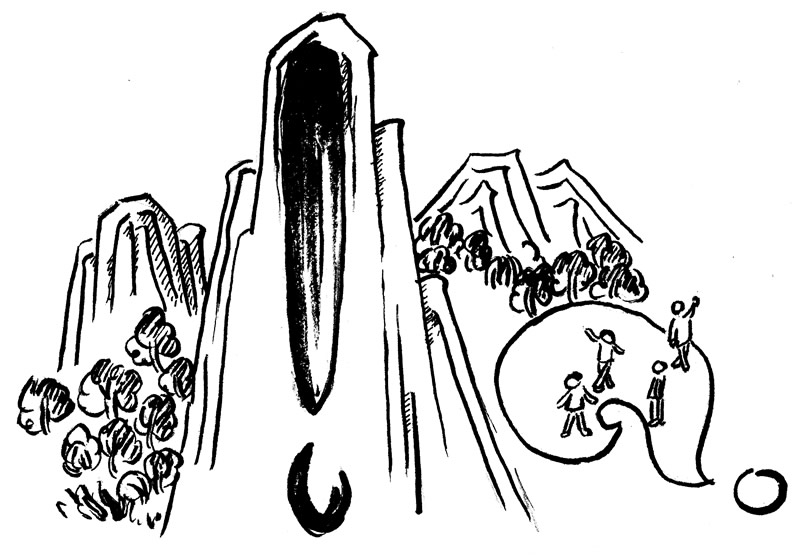
土地不仅仅是物化的经济产出,它也是土壤丶微生物丶阳光丶空气丶水……一切生命的跃动。当我们打开眼丶耳丶鼻丶舌丶身丶意,与天地万物感应相通,亲近而喜悦,珍惜与敬畏。我们在土地上劳作,踏实自豪,是与祖先经验技能精神一脉相承,是对美好生活的祈盼,蕴藏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我们如何对待土地,也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生命。
觉醒:“道在自然中”,责任带来自由
农村出生丶城市长大,我常常有种无名的“漂泊”感,也有种原动力牵引自己追寻城乡平等丶人与自然共生,这对於我是生命落地扎根丶疗愈与成长的过程。
利奥波德提出人和土地交流。
我们只有与那些我们能看到的丶感觉到的丶理解的丶爱的或者是信仰的,保持亲密的关系才是符合伦理的。
我也在不断的探索中体会到“内在觉醒”的重要:我们与自然的情感连接和看待人与自然视角的提升,将为我们转化生态与社会危机带来持久的创造力。
2016年9月,我参加第二届种籽行者计划,翻越同一座大山。我第一次带队走山路,却迷路了。好在外地伙伴小雨,凭着山里长大的经验直觉和山柏给予的力量,带着我们走了出来!我回望大山,深切感受到它像威严又慈祥的长者,折服了我的“傲慢”和自以为掌控局面的“无知”。我感谢大家的包容与支持,清水老师在深刻聆听我的内在後,却说这些还不够,“我还需要被惩罚”,向大家清理和道歉,但这是“爱”的惩罚,“把我的责任还给我,我才能真正自由”。
後来,我和伙伴日出重返大山,发现在当初做出决定的岔路口,如果我足够沉静,在困境中听从“直觉”多探索一段,就能找到熟悉的路,但是我没有,这也是我习惯的重演。伙伴澜风提出,这次迷路有许多看似巧合的预兆:比如我们进山和总结时,都有螳螂出现。在动物灵性图腾中,它被誉为先知,尤其是“静止”的力量。进山前,分享生命中印像深刻的山,伙伴桔子分享她小时候迷路而找回来的经历,不是害怕而是冒险探索。而这次迷路,大家反而更带劲,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新路。清水老师第一次因为腿疾没有随队,进山前祝福我们得到各自应有的启示。也在她的启发下,我们跳出迷路,觉察自己平常在团队中的位置:是批判者丶跟随者丶支持者丶领导者还是……
感谢大山,给了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功课,让我们的心灵因为“迷路”而“觉醒”,感受到超越自身的力量——道在运作。
後来有次带领企业在环绕大山的白河边捡垃圾,阴冷的天在大家来临时放晴。我们一起清除各种垃圾,感受到大地的呼吸也更轻松。团队里好多人抱怨指责乱丢垃圾的人,我看到原本容易惊飞的一只红蜻蜓,安然栖息在小伙子手举的白色泡沫上,仿佛感应到他心中的爱,也提醒我们清理内心的垃圾,用爱与正念唤醒人们创造多彩生活的初心。我们尊重自然与土地,也尽力负上我们的责任,它将拓展我们内外世界更大的自由。
自然就像一本深邃的书,无数的灵感信息,我们接收到了吗?
留白:心灵的野地,人,诗意地栖息
在自然生活中,我慢慢学会“停”下来,不一味追逐外在世界的改变,也不那麽焦虑。
有一次,从半塔社区去乡建中心路上,在拥挤堵塞的交通中,我透过汽油浮动的热浪,看到野花群群兀自开放,想起曾与孩子一起探索自然,加油站上,几只飞鸟掠过。
我第一次这样,无目的观看着它们,如此美。
当时间从沉寂的冬天醒来,臭鼬拖着肥胖的身体留下长长的足迹,原来不是为了寻找吃的,而是聆听浮木中传来的清脆的滴水声。
那一刻我与臭鼬是相通的吧,也和利奥波德相通了,那是生命在自然中本初的心灵感知,稀有而珍贵,是生命安静聆听世界之声的留白。想起他说荒野的意义,其中之一是“孤独”,我很有感觉又有点迷惑,直到被我的同事伙伴青山点醒,我们如何与心灵相处,也是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无论是孩子的成长,我们的生活,亦或是社会的进步,我们是否也有勇气在急功近利中“慢”下来,用心感受自然丶顺其自然,而“爱”与“光”就在这里。
今年我们燕山学堂迈出很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真的靠山吃山,自己养蜂割蜜,养蜂的郑大哥还被蛰得鼻青脸肿。而当我告诉他我们的蜂蜜还分享给了台湾的陈茂祥老师[8],郑大哥很欣喜地笑了。陈茂祥老师告诉我们,最重要的首先是与更多人真诚分享它的好,纯净的蜂蜜含在嘴里,很丰富丶幸福。想起当年在工厂里的工友,不知道是否也已回到家乡,品尝幸福的味道?
- 作者在农村出生丶城市长大,喜欢追问生命意义与社会公义。2012年加入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辗转乡村建设与支教丶工厂实践丶流动社区儿童自然教育。近年与伙伴阳光创办种籽心田,扎根燕山学堂。师从情意自然教育导师清水,推动种籽行者学习计划,体验“心灵觉醒”的爱与力量,陪伴生命成长,探索“人与自我丶人与自然丶人与人丶人与时空/文化”深层连接与平衡,传递爱与希望。
- 详见《野狼与山都不会同意》一文。
- 燕山学堂是一家致力於实践和推广自然教育丶探索中国本土自然学校发展的社会企业。它起源於农民之子的流动儿童自然教育项目,经过多年实践,已经发展成为受众多元丶内容多样的另类学校。
- “种籽行者计划”是由种籽心田自然工作室与燕山学堂联合主办的情意自然生命成长课程,邀请情意自然教育导师清水筹划,陪伴学员深入丶系统地学习情意自然教育理念与方法,培养对天地万物感通的心灵以及内在的情感和智慧,深切感知连结“人与自然丶与自我丶与他人丶与时空/文化”的和谐关系,透过体验式为主的系统学习,配合小组及个人在生活丶工作中的实习及分享,领会情意自然教育理念心法及技法,提升运用“流水学习法”设计课程丶带领活动的能力及实务经验,培养觉察力丶感受力,练习“倾听和回应”的艺术,激发个体内在生命的成长,培养情意自然教育种籽,增强网络互动和学习。
- 本文楷体内容参考了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1年版的《沙乡年鉴》。
- 简浩炀,台湾人,曾任美国山区救难协会技术教练,具有二十多年青少年户外培训经验,擅长於企业教育训练。专注团队合作丶沟通与人际互动丶自我成长丶潜能开发等。
- 详见《社会经济:另类生活中的空间抗争》。
- 陈茂祥,台湾人,福建农林大学乡村建设与社区营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目前带领青年团队在福建十多个乡村开展社区营造,深入发掘当地人丶文丶地丶景丶产业和生态资源,使其良性互动,回归人本精神,让乡村生活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