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春泥[1]
插畫 ▏ 全海燕
每個人心裡一畝田,每個人心裡一個夢,你會用它來種什麼呢?
當我翻閱社區伙伴推薦的《沙鄉年鑒》[2], 我仿佛看到奧爾多·利奧波德和狗走在多年生活的沙鄉農場,懷著愛注視著土地上的生靈自在生息,為他們在“進步”洪流中的消逝而悲嘆、疾呼。他激勵我,回到源頭重新理解“土地”,這串聯起我生命不同階段的體驗,感到內在力量的整合,願更扎實地為土地自然做點什麼。
聆聽:大地上消逝的靈,我們靈魂的挽歌
“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一座山,你印像中最深刻的那座山是什麼呢?”

2015年我參加種籽心田和燕山學堂[3]合辦的首屆“種籽行者計劃”[4],在翻越一座大山前,清水老師問我們。我想起家鄉的山,那裡自然純淨、親情厚重。河水、稻田、青山,清晨淡淡的霧縈繞竹林,黃昏爺爺頂著晾曬菜干的竹篾回家。有次家鄉發大水,他翻進窗戶,搶背出年邁的太奶奶。當我大病回鄉,家人帶我上山,爸爸找筍一找一個准,從小帶我的奶奶已經滿頭白發依然身手敏捷,查看地形告訴我們有野豬,我感到山的溫情與神秘威嚴。
所以,當我看到《沙鄉年鑒》,山和熊的故事,我特別難受。
艾斯卡迪拉山,有一個神秘而確鑿的存在,那就是大灰熊,它本是當地人們生活閑談不可缺少的話題。每年春天,它會從冬眠中醒來,下山吃掉一頭牛,然後爬回洞穴,靠著土撥鼠、蹄兔、漿果和樹根,悠閑地度過夏天。然而當“進步”之風刮來,人們開始關注駕車橫穿美國大陸、婦女投票權,甚至有老人好奇電話線能否送來熏肉,最後來了一位捕獸員,用盡各種辦法殺死了熊,它甚至無法留下一張像樣的皮。
從創世之初,歲月不斷在這座古老的山脈留下印記:莊嚴的外表、較小的動植物群落和一只大灰熊。[5]
而熊,死了。沒有熊的艾斯卡迪拉山,也“死”了,盡管它依然威嚴聳立。
有多少大地上流動的靈正在逝去,誰來定義“進步”,誰在發展“權利”的同時負責?
威斯康星州野生火雞、赤鹿被滅絕,最後一群旅鴿變成餡餅。田鼠啃光了許多年輕果園裡的果樹皮。一頭憤怒的奶牛引發了1871年的大火。過度種植小麥的土地失去肥力。麥迪遜的春花比往年足足晚了十三天。無雪的冬天,可憐的蘋果樹紛紛被凍死。葉蜂流行病摧毀好幾百萬美加落葉松。沼澤的水被抽干開辟農田,卻成了廢墟……
我想起簡浩煬老師[6]問,“你們可曾親吻過大地?”如果我們感受過她母親般的胸懷,體會飛鳥野花樹木自在繁衍生息之美和獨特的生命故事,正如我們的兄弟姐妹與鄰居,我們是否會對他們的逝去,無動於衷?
我們以為保護的是熊,其實是整座山和它的歷史。
處在生物金字塔頂端的人類,無視和掠奪支撐著我們的土地的自然生命,死去的也是我們的靈魂。
反省:重建人與人、人與土地的連接
當我聽到地鐵邊賣水果的父親訓斥兒子“不好好讀書,將來就像我一樣”,格外心酸。我們怎樣去看待“教育”對於時代的意義呢?正如利奧波德提醒我們,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人群分崩離析的危機,同樣也發生在人與土地構成的群落。在城鄉差距、工農業剪刀差、消費文明等影響下,農村人潮湧入城市,而那裡卻並非夢想中的世界。土地、空氣、水、光電處處污染,我們失落的不僅是土地,更是它所承載的文化自信、勞動者的尊嚴、人與人的信任。鄉土的消逝亦是文化自信的消逝。
經濟需要有道德與美學的前提。我們的一切,如美好家園、更好的教育,都要有利可圖嗎?經濟的力量,應該是驅動社會組織的方方面面,與我們這些前提和諧相處,更可持續地生活。
我也曾每天在流水線前站十多個小時,因手笨完不成既定產量被訓而哭;當成為熟練工後,卻在夜班時倚著機器感到“絕望”。工廠裡有人說茫茫人海自己像小草一樣被淹沒,有人整晚加班天快亮時一松神被機器打到傷殘;單打獨鬥維權困難重重……
我始終記得,一個工友姐妹和我說,她想回家,她想回家養蜂。
那一瞬間,驚醒了我,我看到長期被輕視、需要被拯救的“鄉土”的意義,也正是它,在城市金融危機工廠倒閉之時,擁抱大量失業回鄉的人們。
半塔村是個打工人群聚集生活的流動社區,人與人彼此間的關系比較陌生,我們在“農民之子”[7]辦起社區廚房,用“食物”連接土地、分享生活,拉廢磚運土砌花壇種蔬菜。在飯店當大廚的爸爸第一次發現兒子自己做飯原來這麼好吃!孩子媽媽教我們腌鹹菜。山西小伙兒的臊子面是記憶中媽媽的味道。社區修自行車的大哥慷慨提供冰箱存放我們手作的健康冰棍。一起過“中秋節”,掛燈籠、猜燈謎、烤月餅、拜月亮,祈福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提著親手做的燈籠走過平日嘈雜的街巷,流動的光,大人看到自己的童年,孩子追著我們跑……自然和社區是我們的教室,身邊人是我們的老師,在奔波生計中點亮心靈的光,喚起對當下“美好”的追求,生活也有不依賴“錢”的更多可能,由我們彼此分擔、一起創造、共享情意自然。
燕山懷抱長城之畔,我們在燕山學堂和志願者、孩子一起造“土”?!整地、打木樁籬笆、鋪廢紙皮、撿樹枝,放上長期積累的廚余,倒上木屑,一起為它們祝福,期待長出“新”土種蔬菜!孩子念念不忘,廚余的味道真是太酸爽了!在記憶中,已有一小塊土壤播下了種籽,有惜福、感恩、互助、堅持、期盼……那是在親近土地勞作中美好的品質。因為付出過,我也會時常照顧這小塊地,當我看見木屑堆上長出幾顆晶瑩剔透的菌菇時,我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流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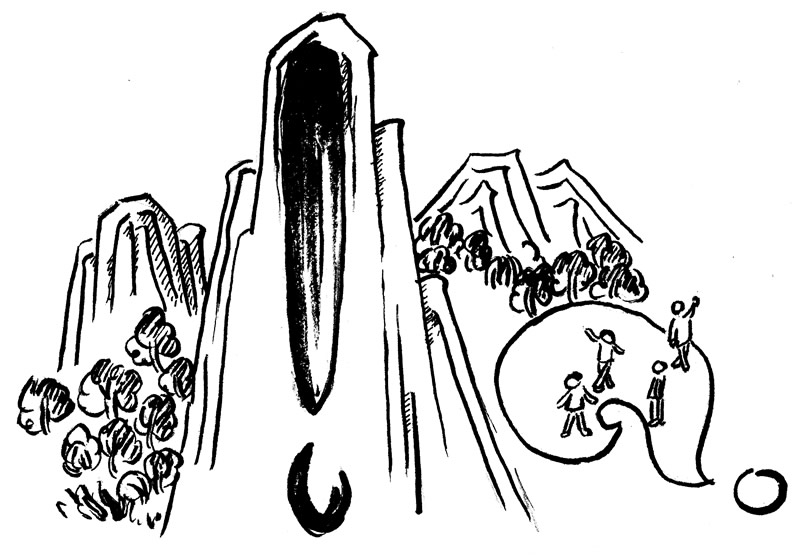
土地不僅僅是物化的經濟產出,它也是土壤、微生物、陽光、空氣、水……一切生命的躍動。當我們打開眼、耳、鼻、舌、身、意,與天地萬物感應相通,親近而喜悅,珍惜與敬畏。我們在土地上勞作,踏實自豪,是與祖先經驗技能精神一脈相承,是對美好生活的祈盼,蘊藏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我們如何對待土地,也是如何對待我們自己的生命。
覺醒:“道在自然中”,責任帶來自由
農村出生、城市長大,我常常有種無名的“漂泊”感,也有種原動力牽引自己追尋城鄉平等、人與自然共生,這對於我是生命落地扎根、療愈與成長的過程。
利奧波德提出人和土地交流。
我們只有與那些我們能看到的、感覺到的、理解的、愛的或者是信仰的,保持親密的關系才是符合倫理的。
我也在不斷的探索中體會到“內在覺醒”的重要:我們與自然的情感連接和看待人與自然視角的提升,將為我們轉化生態與社會危機帶來持久的創造力。
2016年9月,我參加第二屆種籽行者計劃,翻越同一座大山。我第一次帶隊走山路,卻迷路了。好在外地伙伴小雨,憑著山裡長大的經驗直覺和山柏給予的力量,帶著我們走了出來!我回望大山,深切感受到它像威嚴又慈祥的長者,折服了我的“傲慢”和自以為掌控局面的“無知”。我感謝大家的包容與支持,清水老師在深刻聆聽我的內在後,卻說這些還不夠,“我還需要被懲罰”,向大家清理和道歉,但這是“愛”的懲罰,“把我的責任還給我,我才能真正自由”。
後來,我和伙伴日出重返大山,發現在當初做出決定的岔路口,如果我足夠沉靜,在困境中聽從“直覺”多探索一段,就能找到熟悉的路,但是我沒有,這也是我習慣的重演。伙伴瀾風提出,這次迷路有許多看似巧合的預兆:比如我們進山和總結時,都有螳螂出現。在動物靈性圖騰中,它被譽為先知,尤其是“靜止”的力量。進山前,分享生命中印像深刻的山,伙伴桔子分享她小時候迷路而找回來的經歷,不是害怕而是冒險探索。而這次迷路,大家反而更帶勁,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新路。清水老師第一次因為腿疾沒有隨隊,進山前祝福我們得到各自應有的啟示。也在她的啟發下,我們跳出迷路,覺察自己平常在團隊中的位置:是批判者、跟隨者、支持者、領導者還是……
感謝大山,給了我們每個人獨特的功課,讓我們的心靈因為“迷路”而“覺醒”,感受到超越自身的力量——道在運作。
後來有次帶領企業在環繞大山的白河邊撿垃圾,陰冷的天在大家來臨時放晴。我們一起清除各種垃圾,感受到大地的呼吸也更輕松。團隊裡好多人抱怨指責亂丟垃圾的人,我看到原本容易驚飛的一只紅蜻蜓,安然棲息在小伙子手舉的白色泡沫上,仿佛感應到他心中的愛,也提醒我們清理內心的垃圾,用愛與正念喚醒人們創造多彩生活的初心。我們尊重自然與土地,也盡力負上我們的責任,它將拓展我們內外世界更大的自由。
自然就像一本深邃的書,無數的靈感信息,我們接收到了嗎?
留白:心靈的野地,人,詩意地棲息
在自然生活中,我慢慢學會“停”下來,不一味追逐外在世界的改變,也不那麼焦慮。
有一次,從半塔社區去鄉建中心路上,在擁擠堵塞的交通中,我透過汽油浮動的熱浪,看到野花群群兀自開放,想起曾與孩子一起探索自然,加油站上,幾只飛鳥掠過。
我第一次這樣,無目的觀看著它們,如此美。
當時間從沉寂的冬天醒來,臭鼬拖著肥胖的身體留下長長的足跡,原來不是為了尋找吃的,而是聆聽浮木中傳來的清脆的滴水聲。
那一刻我與臭鼬是相通的吧,也和利奧波德相通了,那是生命在自然中本初的心靈感知,稀有而珍貴,是生命安靜聆聽世界之聲的留白。想起他說荒野的意義,其中之一是“孤獨”,我很有感覺又有點迷惑,直到被我的同事伙伴青山點醒,我們如何與心靈相處,也是我們如何與世界相處。無論是孩子的成長,我們的生活,亦或是社會的進步,我們是否也有勇氣在急功近利中“慢”下來,用心感受自然、順其自然,而“愛”與“光”就在這裡。
今年我們燕山學堂邁出很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真的靠山吃山,自己養蜂割蜜,養蜂的鄭大哥還被蟄得鼻青臉腫。而當我告訴他我們的蜂蜜還分享給了台灣的陳茂祥老師[8],鄭大哥很欣喜地笑了。陳茂祥老師告訴我們,最重要的首先是與更多人真誠分享它的好,純淨的蜂蜜含在嘴裡,很豐富、幸福。想起當年在工廠裡的工友,不知道是否也已回到家鄉,品嘗幸福的味道?
- 作者在農村出生、城市長大,喜歡追問生命意義與社會公義。2012年加入北師大農民之子社團,輾轉鄉村建設與支教、工廠實踐、流動社區兒童自然教育。近年與伙伴陽光創辦種籽心田,扎根燕山學堂。師從情意自然教育導師清水,推動種籽行者學習計劃,體驗“心靈覺醒”的愛與力量,陪伴生命成長,探索“人與自我、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時空/文化”深層連接與平衡,傳遞愛與希望。
- 詳見《野狼與山都不會同意》一文。
- 燕山學堂是一家致力於實踐和推廣自然教育、探索中國本土自然學校發展的社會企業。它起源於農民之子的流動兒童自然教育項目,經過多年實踐,已經發展成為受眾多元、內容多樣的另類學校。
- “種籽行者計劃”是由種籽心田自然工作室與燕山學堂聯合主辦的情意自然生命成長課程,邀請情意自然教育導師清水籌劃,陪伴學員深入、系統地學習情意自然教育理念與方法,培養對天地萬物感通的心靈以及內在的情感和智慧,深切感知連結“人與自然、與自我、與他人、與時空/文化”的和諧關系,透過體驗式為主的系統學習,配合小組及個人在生活、工作中的實習及分享,領會情意自然教育理念心法及技法,提升運用“流水學習法”設計課程、帶領活動的能力及實務經驗,培養覺察力、感受力,練習“傾聽和回應”的藝術,激發個體內在生命的成長,培養情意自然教育種籽,增強網絡互動和學習。
- 本文楷體內容參考了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2011年版的《沙鄉年鑒》。
- 簡浩煬,台灣人,曾任美國山區救難協會技術教練,具有二十多年青少年戶外培訓經驗,擅長於企業教育訓練。專注團隊合作、溝通與人際互動、自我成長、潛能開發等。
- 詳見《社會經濟:另類生活中的空間抗爭》。
- 陳茂祥,台灣人,福建農林大學鄉村建設與社區營造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目前帶領青年團隊在福建十多個鄉村開展社區營造,深入發掘當地人、文、地、景、產業和生態資源,使其良性互動,回歸人本精神,讓鄉村生活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