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萧依萍
寻寻觅觅中,当我从一个旁观者转变成实践者,我终于理解伙伴们以前经常在不同机构与不同位置转来转去、摸不清方向的感受了。这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周旋,也是在统一和矛盾之间辗转的状态。
对我来说,可持续生活是一种革命,一种自下而上的生活革命。它意味着去改变生活中的种种,尤其是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消费主义、家庭单元化、昔日族群间相互依存的生活体系被减弱、对弱势群体如农夫、工人群体的压榨与剥削,这些看似与我们现代化的生活无关,可是当我们被消费主义所薰陶,渐渐对不公不义视若无睹时,我们也是帮凶之一。
初踏务农之路
离开社区伙伴是因为觉得既然自己相信可持续生活的理念,亦在推行此事,与其拿一份固定工资鼓励别人去做(而且还不知是否可行),倒不如在前线作为实践者,先去实验所相信的是否可行。
实践过程中,我渐渐发现资本主义是一个运转已久的巨轮,想要逆转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其中夹缝求存。这是从空中落到地上,脚踏实地时所感到的自觉,也是一位务农前辈的肺腑之言。人总要吃饭,而现实是你不一定能种出所有生活所需的品种和数量,而且就算找到一块地,亦要交付租金,所以你还是逃不过资本主义的巨轮。
最初以耕作作为实践可持续生活的途径是源于体验假日农夫时感受到对农业的兴趣,而如果谈到生活,粮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个世界非常需要农夫,也因为农村社区发展的工作经验,让我更希望自己成为过去服务对象——农夫的一份子,一起改变世人对农夫的刻板印象。
因为从过去的工作中看见过一些起起伏伏,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对田园生活的美好想象,也知道农业博大精深,并不那么容易掌握,可是过程中还是走了很多弯路。离职后第一阶段的务农生活是跟随一位已具四十多年耕作经验、我们称她为婆婆的有机农夫学习,与我同行的共有三人,我是团队中的半职人员。虽然是半职,但仍然体会到了农夫的艰辛和体力的透支,因为工具使用不当,团队四人中有三人,包括我都患上了“弹弓手”(腱鞘炎)。
在乐田园(婆婆的农场)的日子,是一个帮我蜕掉假日农夫时对自然的欣赏和兴致的阶段。与假日农夫不同,此时要考虑产量,速度即效率。我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农活,割草整行割、种菜种不停,我们似乎变成了工厂女工,重复着单一的动作,速度成为了第一个考验的关卡。最初我们四个人都被婆婆说太慢了,与偶尔来农场的女工相比,我们四个人加起来都没有她一个人的效率高。
坦白说,即使到现在我的速度也比不过农家姐弟,但比初入行时是略有进步了。
第一关是速度,而在乐田园的第二关就是眼界,为什么种田跟眼界有关?
种菜株行距很重要,因为会影响后期中耕除草,所以婆婆对于行距的要求较高。我们新手当然眼界不准,常把菜种得歪歪斜斜,后来婆婆给我们每人发一枝竹仔,让我们量行距,最初心里都不以为然,到中耕时就自食其果了。因为考虑生产属性,同一田垄都只会种单一的作物,与过去生物多样性的思考截然不同。但后来发现,这是在农业生产中因产量的需要、作物的管理而必需的。
除了体力和意志的磨练外,参与其中才看到有机行业中的黑暗面,以前以为美好的人和事其实也有邪恶和虚伪的一面。例如有个农场给超市供有机菜,但每每我们路过农场,里面都是野草丛生,他们供超市的菜从哪里来就不言而喻了。农夫也是人,农夫并非一定是弱者,也并非一定是好人,人性都是共通的,世界本是如此,与行业无关。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寻求真相,而不是美化某一个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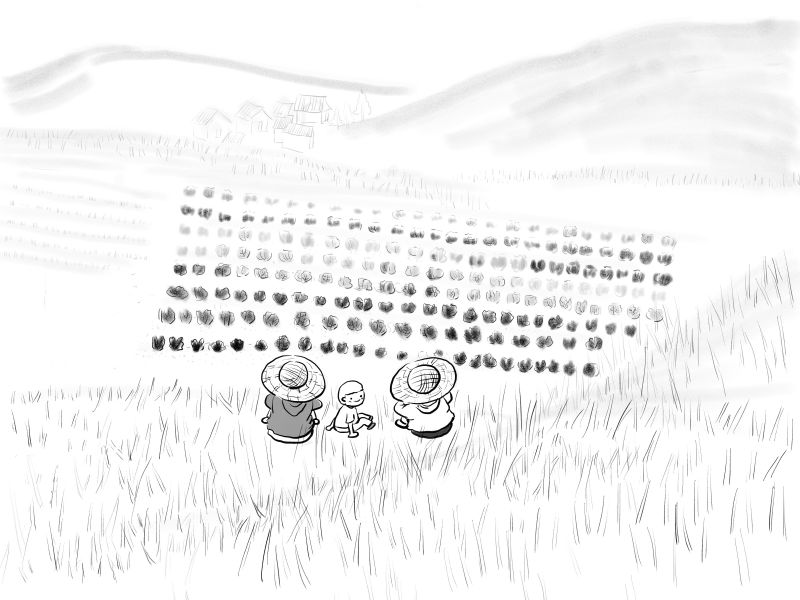
另一条探索之路
后来一方面觉得团队不合,一方面看不到前路,我决定离开乐田园。在我打算离开之际,一位朋友愿意借田给我,教我务农之技,还给我介绍兼职。于是我就展开了一边兼职,一边耕作的生活。
在朋友的农场,我从学习使用锄头开始。在乐田园是没有人教我们如何运用工具的,都是自己看着用。重新学习后才发现原来用锄头不是用蛮力,而是要把力用对、用巧——破土而入,震开土块,锄地要有节奏,不能一味地心急逞快。从使用锄头到如何撒播、如何挖坑、如何育苗、肥水管理和农场管理都需要重新学习。我非常感激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和拥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
拥有自己的一小片地,让我重拾对植物和自然的兴味,如何规划是农耕中最有趣的部分。开荒的过程还是比较艰辛的,因为没有割草机,只能用锄头,但看着荒原慢慢长出菜来,还是让人高兴,例如第一次成功种出榨菜、种出火姜等。虽然种得不是很好,可是种出自己喜欢的菜是一个愉悦的过程。第一年因为是新地,大部分作物都长得不错,但长得散漫自由,缺乏农业生产中的规整,没有产量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年我开始逼迫自己种得更规整,作物也都种得比之前好一些,但因为错过了合适的采收时间,导致菜无法出售。第二年我也更专注地做腌渍,自己开始对腌渍这件事有感觉了,其实腌渍和耕种一样,都要以照顾的心情去对待你的作物或渍物,时刻观察它们的状态,慢慢地你就会有种该如何做的直觉。当然理论知识的框架也是很重要的。
这数年间一直都希望可以以农业为生,但从未实现。我一直依靠兼职而非卖农产品为生,这是在乐田园时就已有的状态,一是因为菜没有种好而产量低,二是因为规模不足,因此产量也不足以供应一些较大的客户,没有足够稳定的菜量,留不住大客户,收入也就不稳定,这是“鸡先或蛋先”的问题,其实也是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这也是香港有机农业的问题,多样化的农场在管理上需要花的时间、心思较多,最重要的是技术要求较高。香港农墟的有机菜价已被抬高至很不合理的价格,因此有机行业并不是面对大众的市 场,而不合理的高价亦让支持者变得望而却步,这也是这些年农墟生意慢慢萧条的原因。所以回到基本点,还是产量不足和缺乏良好规划的问题,而产量其实还是技术的问题,也是我要面对的难题。
求学自知与平心见志
步入务农的第三或第四年,我决定去台东一趟。自己一直想从事自然农法,更想做一个有产量的自然农夫,于是去了台东求学,也有一种还债的心态。虽然很多人都建议不要去,但我还是想去,就去了。
在台东这一年,除了回港工作的时间,就是天天务农,天天的意思就是一周七天。老师不会说很多,多数时候他让你自己观察得出结论,他再回应你。问问题不能是开放式的,要自己思考到底答案是是还是否,是一还是二,再跟老师确认。
在台东这一年,积累了许多自己的观察,棱角丝瓜和圆形丝瓜虽然同是丝瓜,但开花、授粉的时间都不同,所以套袋的时间不同。哈密瓜之前没有种过,不知怎样的状态采收最好,试了几次才真正掌握采收的时间点,吃上了又香又甜的哈密瓜。我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适地适种,如何才能让一天的草没有白割。算是学到一点东西,但在即将离开之际,才发现原来不懂的还很多。
然而,台东之行后我更清晰了自己的方向,不是成为大型生产的农夫,而是小型生产兼农产品加工,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也是好事一件。另一个收获是在日常的劳作中,让心情处于自然之中得以平静,让原本在香港繁乱的心得以平伏。
我一直问自己务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最初是希望自己能做一个靠自己的双手生活的农夫,想改变农夫的地位,改变世人对农夫的眼光。但自己务农又是否可以达到这一目标?好像不然。慢慢地,我希望这是一种生活状态,务农和与人相处都是我喜欢的事情,如何把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推广给他人是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务农期间,一直都未能靠务农为生,而似乎这个目标也还很远。作为一个城市人,自己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就可以学到精湛的技术、然后赚大钱、改变人们对农夫的看法。农艺博大精深,其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学一辈子都学不完,永远有新鲜的事物在路上。
未来的路不知会如何走下去,但估计多多少少跟农业脱不了关系。坦白说,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执着于务农,对务农就是有种难以放下的挂念。我想,或许是由于过去在农村工作的关系,亦或许这就是命运吧。曾有人问我,你会如何把生产、生态、生活排序,孰先孰后?作为一个以农为生的人理所当然是以生产为先,没有生产,何谈生活。但对现在的我来说,我更希望这“三生”是一个平衡相生的状态。

■ 萧依萍 八年NGO的工作经验,五年在宣明会宁夏驻点做农村社区发展工作,三年在社区伙伴做大陆社区支持农业的推动工作。自离职后,一直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希望把所相信的理念带到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