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安生活的在地探索
文 ▏ 張鳴[1]
插畫 ▏ 全海燕
一眨眼,天安就三歲了。我和劉瀟,兩個城市青年,從開始僅僅為了滿足自身需要去尋找可靠的食物,到今日慢慢想做一個扎根四川、服務小農的平台,我們蹣跚學步走過了一千多個日日夜夜,和身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吃的方式,尊重自然,學會生活。
從一個蘋果開始的天安
2013年11月,我去劉瀟的辦公室買小金蘋果。因為我倆都是生態農產品的消費者,又參與過成都CSA[2]的志願者服務工作,自然有很多共同的話題。我們一邊吃,一邊聊起這個蘋果的過往。
2012年,我們就已經吃到了小金蘋果。當時,社區伙伴的項目官員聯系成都志願消費團體“綠心田”[3]創始人之一的夏路,希望能幫小金農友賣蘋果。基於對社區伙伴的信任,團購信息很快在“綠心田”的消費者群發出,200箱蘋果隨即從小金運到成都。當時,我是綠心田的志願者,在家小區門衛室設立了一個取貨點。
那時的蘋果一箱有40斤,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就一個紙箱裝著,經過長途運輸,難免磕碰,賣相不好。而碰壞的蘋果,往往就分給我們這些志願者。那時候,我還跟夏路抱怨,“同樣是出錢買蘋果,為什麼我們就要拿最差的?”得到的回答總是“呵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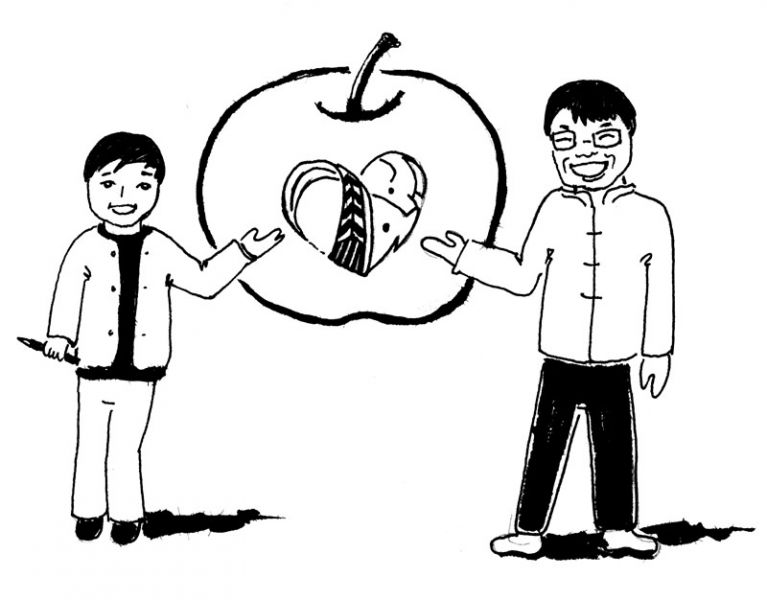
“蘋果好吃,小金的農產品也不錯,咱們弄點兒出來,自己有得吃啊……”我提出建議,但又有顧慮:“如果繼續像過去以志願者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效率不高,不穩定,所有事情都壓在幾個志願者身上,耗費人力和心力,最後卻不了了之。有沒有可能找到一種更可持續的方式來做這樣的城鄉連結,讓農友的產品能夠完好順利到達消費者手裡,而消費者持續的購買又能支持到友善農耕的農友,形成良性互動的支持體系。”
“其實大家對好的農產品是有需求的,只是大部分消費者不知道如何辨別,到哪裡去買。我們可以試試,你來把農友的故事寫出來,我負責賣,咱們把最真實的農產品生產過程展示出來,讓消費者自己來選擇。”劉瀟回應說。
就這樣,一邊吃蘋果一邊聊,我們對將要做的事情充滿了迫不及待的勇氣和信心。雖然我和劉瀟都不是學農出身,也沒有專業背景,但我們希望通過努力,一方面滿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能把優質的農產品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借此為農人發聲,讓大家了解堅守土地的農人,引導城市消費者用共同購買的方式支持友善農耕,進而重新構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互助關系。
一切都在摸索中開始。2013年12月17日,我們通過天安生活的微信公眾號發布了第一篇實地探訪四川遂寧廖勇農場的故事,向消費者推薦廖勇生態種植的蓮藕,開啟以可持續方式支持友善農耕的探索與實踐之路。
天安CSA實踐:與農人同心
成都是國內實踐CSA較早的城市,擁有資源豐富的農村和實驗生態農業的群體。我們開始做天安之後,才發現四川地區的生態小農和返鄉青年的需求巨大,這也堅定了我們想要做一個立足成都、扎根四川、服務小農的平台:以生態農產品為主線,協助農友,提升與產品的連結能力;進行農事傳播,提升與消費者的連結能力。
和農友打交道,我們首先要學習如何跟他們做朋友。我們堅信,選擇產品的前提,是先找到踏實做事的人,再通過觀察和交流,尋找可靠的產品。我們希望農友的產品各有特點,品質優秀,能滿足消費者的生活必需。這個過程中,農友需要花費精力不斷完善農產品,而我們能做的就是陪伴與協助。
王雪梅的故事,也許能說明些什麼。
雪梅是檸檬君張揚[4]的表姐,為了陪伴孩子,不願女兒成為留守兒童,她放棄了成都的小生意,於2014年3月返鄉。受張揚影響,雪梅很快接受了生態農業的理念,希望能以此養家糊口。
不用農藥、化肥和除草劑種地,不但產量低收入少,還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雪梅做生態農業初期,步履維艱。2014年6月,她邀請成都生活市集工作人員去她家考察。那時候,雪梅家除了蔬菜,還有幾十株生態李子即將成熟,但長勢並不好。看樣子,雪梅能賣的產品不多也沒特色,我們暗自為她擔心。聊著聊著,劉瀟建議雪梅說,“你們丹棱出凍粑[5],你做凍粑來賣,沒人和你競爭的啊。”說干就干,第二天,雪梅就去找師傅學做凍粑。她花了三千塊在丹棱縣城最好的凍粑店學習了三個月,然後回家研究,用自家的生態大米,制作無添加的凍粑。
2014年9月,雪梅開始在生活市集和生態產品消費圈賣生態無添加的丹棱凍粑,備受消費者歡迎。
剛開始,雖然銷售看起來不錯,但是凍粑也有很大局限。夏天,沒有防腐劑的凍粑不易運輸和保存,所以基本上無法制作凍粑銷售。為了彌補空檔,2016年初,雪梅又花了五千塊去學習制作豆腐干,她的丈夫陳二娃也因此回家幫忙。不久,凍粑和豆腐干的制作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有相對穩定的客源,在外人看來,雪梅選擇的生態食品加工是條可行之路,既能照顧家庭,又有不錯的收入。
然而,個中的過程還是有我們想像不到的困難。2016年9月的一天晚上,雪梅在“天安生活交流群”發了一段長長的話:
陳二娃一點左右做好了豆干,我剛好被蚊子咬醒,睡眼朦朧地找他點蚊香。他突然來了一句“想出去打工了,打工了,打工了……”一瞬間我睡意全無。“現在的收入維持不了我們一家老小的開支……”
很多人會覺得生意挺好的,為啥就維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呢?我只能“呵呵”了。我是從9月份開始每周發一次貨,每一次的總營業額就1200至1800元之間。除掉所有的開支純利潤只有幾百,我們家每個月的開支包括車油錢600-800元左右,孩子200-300元左右,話費300-500元左右(因為有支付寶、微信支付,經常會有長輩讓幫充話費,充了也會不好意思要錢)。
所以一家三口一直過得緊巴巴的,車小了想換個面包車都惱火。今天為了增加銷路,小陳還去擺地攤,看看能不能走普通市場路線(想著薄利多銷)。今天去虧本賣了43塊回來,連黃豆的成本都沒收回來。在菜市場因為一孕婦暈倒了,陳二娃中途好心送了孕婦去縣城醫院。我還埋怨他為啥不打120急救,要是真出啥事負不了責。
陳二娃一回來就很氣餒,看來實體店銷售這條路走不通。直到剛剛他和我談話,我才覺得他是真的想去打工掙錢了。那以後我咋辦,一個人做凍粑、豆干?就是把我裝上發條我也做不出來。
看到這裡,我五味雜陳。給雪梅回信息鼓勵的同時,立即跟天安的伙伴商量,發起一次凍粑和豆腐干的團購——關鍵時刻,我們希望能陪伴雪梅再堅持一下。當晚,我寫了一篇《雪梅,我們支持你》的文章,發布在微信公眾號。沒想到,看到文章的朋友和消費者大力轉發,來自全國各地的凍粑訂單急速增長。我們在微信建了一個“天安-雪梅”的工作群,有雪梅、劉瀟、店長和我。那些天,店長一直在微店和微信上忙活,回答客戶問題、整理訂單、發送訂單、監督訂單快遞配送,每天工作到凌晨一點。雪梅一家更是辛苦,起早貪黑制作凍粑和豆腐干,包裝發貨。而此時,我能做的只有鼓勵。我給雪梅說,“雪梅,你就辛苦這一段時間,消費者可能會因為同情支持購買,但是情懷不能賣很多次,唯有把產品質量做好,才能把消費者變成你的長期客戶。”
就這樣,雪梅堅持了下來。
日常銷售中,雪梅其實也有自己的微店,但她經常喊顧客到天安下單。事實上,農友也很忙,客服是很耗費精力的,從長遠來看,各自做擅長的工作,分工更明確,是一個方向。像天安這樣的中間平台,價值就在於幫助農戶處理客服工作、物流快遞、訂單追蹤等等,讓消費者覺得買到的產品物有所值。這個過程,需要相互的支持、努力和探索。
通過這樣的緊密配合,天安以產品為主線,協助農友建立與產品的連結能力,加上傳播,建立與消費者的連結能力。這是天安三年以來,服務小農的點滴經驗和感受。
努力成為從農場到餐桌最近的路
我們始終認為,生態農產品要脫穎而出得到消費者認可,品質和口感是很重要的。除了生態種植,還需要妥善的運輸。
每年一到吃大櫻桃的季節,我們總是又愛又恨。愛的是它的口感,好吃到讓人停不了口。恨的是它太嬌嫩,不得不讓我們絞盡腦汁考慮妥善的辦法,把它送到消費者的手裡。
總結往年費力不討好的經驗,我們今年采用了費力但是討好的辦法,賣小金的大櫻桃。
5月底,天安團隊伙伴們一起前往小金實地探訪。這是每年售賣小金大櫻桃前都要做的工作。除了采集素材為宣傳做准備之外,最重要的是跟農友溝通,確定櫻桃的采摘和挑選標准:按照發貨地點,確定櫻桃的采摘成熟度。成熟度高的櫻桃,在成都本地銷售;成熟度相對低一些的櫻桃,發往外地。基於過去兩年的經驗教訓,今年跟農友的溝通比較順暢,農友在采摘和挑選上也能和我們的要求達成一致。“壞的果子,不賣”,一句從農友口中說出的簡單的話,化作實踐時,真需要反復嘗試,當中包含了農友和我們共同的努力。
接下來的挑戰是運輸。往年的櫻桃都是采摘後,用小汽車運出來。512汶川地震後,成都到小金的路段損毀,加上每年夏天泥石流災害,路途非常顛簸,嬌嫩的大櫻桃到達成都後,常有很多損壞。今年我們花高價協調了一輛物流冷運車,農友采摘後直接裝車冷鏈,經過7、8個小時的運輸,到達成都機場的冷庫,再加入冰袋保鮮包裝,當晚直接通過航班發往全國各地。
在當時接近30度的高溫下,冰袋只有10個小時的保鮮時間,第二天一早,我們就開始追蹤訂單,看櫻桃是否及時送到消費者手中。越來越大的城市範圍、日漸升高的溫度以及無法徹底解決的保鮮難題,都是生態水果運輸的痛點。
考慮到大櫻桃的成熟度增高,不再適合長途運輸,我們果斷停止向外地發貨。減數量保質量,成為最後幾批大櫻桃售賣的宗旨。首先,我們限定了配送區域:以辦公室為中心輻射到的南一環和南三環之間。然後,確定每一批只銷售20份大櫻桃。農友通過小車在下午運到成都,我們簡單挑選後,立即通過同城的快遞公司進行配送,最快可以在半小時之內送到消費者手裡。
這樣的銷售,在別人看來很不起眼,但於我們卻是有意思的嘗試。第一,它減少了運輸裡程,幫助農友把往年成熟度極高賣不掉的大櫻桃賣出去,既能與消費者分享,也讓農人得益。第二,優化了從農場到餐桌的流程,減少產品損耗,快捷及時送達消費者,不讓優質的生態產品輸在最後一公裡。
講好農人故事的攝影師才算合格的賣貨郎
以前我是媒體攝影記者,現在我更願意稱自己是“農藝師”——以農村天地為藝術創作的攝影師。在過去的三年裡,我背著相機走過了幾千公裡的鄉村路,跟農友交朋友,學習土地和生活的智慧。

這本身就是一個在學習中成長和充實的過程。翻看過去寫的文章,由於自己對生態農業的了解還不夠深入,僅停留在某個農人做某件事的層面,不能把其中的道理,用符合大眾傳播的語言講述出來。當有一定數量的農人故事積累後,我的追問開始深入:為何要做?如何做?之後,我通過微信公眾平台,以“一個人物+一個故事+一個農產品+一種態度”的形式,講述農人的故事,向讀者推薦他們的生態農產品。在我看來,這樣的傳播是一種友好的表達方式、有效的溝通工具,它是開放的、自由的、有取舍的、有創造的。
例如對小金蘋果的傳播,從種植到餐桌,有很多信息需要傳遞出來。一開始,實地探訪農友的種植方式,地理環境的情況,給消費者以直觀的感受,從而了解產品背景。實地探訪的文章每一年都會有,既記錄了農友的生產過程,又向消費者傳遞真實的產品信息。除此之外,為了給大家講蘋果怎麼變著花樣吃,我們邀請熱心的消費者將蘋果加工成果醬、蘋果撻等等,記錄下做法,寫成文章傳播出去,於是有了小金蘋果的系列文章。這樣的方式,既增進了與消費者的互動交流,也實現了分享傳播的目的。
一個小小的蘋果,花這麼多力氣去推,是因為我們認為,好的產品除了要在生產端嚴格把控質量之外,還應該做足消費者教育的工作,深入淺出地傳遞食物背後所蘊含的理念與精神。
不會講故事的攝影師,不是一個好的賣貨郎。當俯身土地,我發現沉默的相機能做發聲的武器。照片可以傳遞尖銳批判,也可以釋放溫柔情意。跟過去相比,我現在的照片和文字少了衝突、起伏,多的是隨意、平和。2015年,在朋友的推薦下,我去四川眉山參觀一家竹纖維造紙廠。過去我們對造紙廠的印像是污染、劇毒、不能靠近,但是這家紙廠的環保工藝流程卻給我留下很深的印像。後來我寫了一篇《一張紙的生活意見》,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從竹子到一張竹纖維紙的變化,講述個中故事。從那以後,我自己變成了竹纖維紙的消費者,並帶動身邊的朋友選擇竹纖維紙。與其誇誇其談,不如親身實踐。用專長去把故事講好,是我一直以來努力學習和提高的能力。
每每聽到別人對天安的肯定和贊美,我總是很慚愧。天安走到現在,並不是為農人、為大家做了什麼,而是天安讓我們深刻體驗到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在與土地相處的過程中,我們嘗試探索一個可行的方法,和大家一起,以吃的方式,尊重自然,學會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