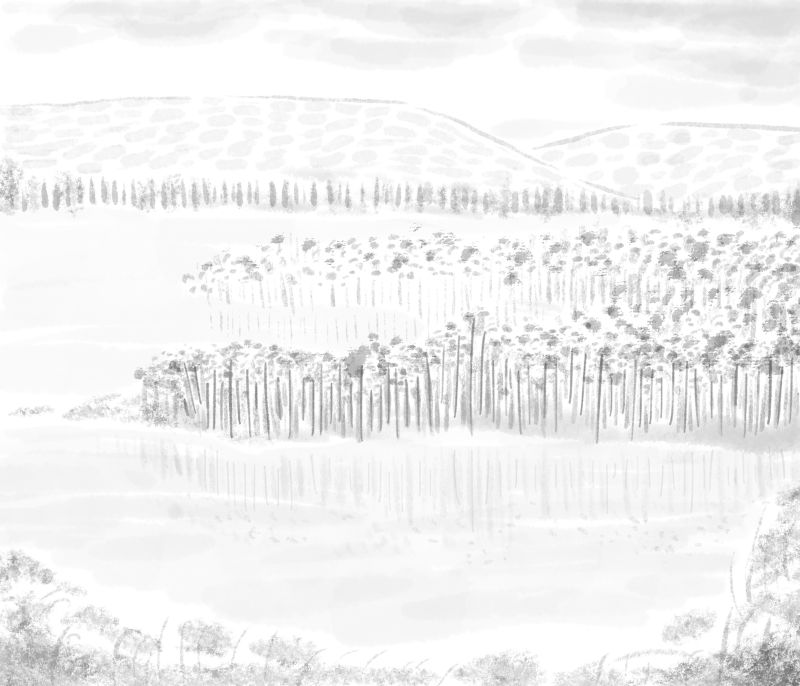文 | 阿乐
都市人与自然环境的距离
2018年9月,台风山竹吹袭香港,为这个先进城市带来不一样的景象:海边翻起四五层楼高的浪,好些大厦玻璃幕墙被吹烂,整个工程天秤从二十几楼被吹倒下来…… 翌日,香港市民如常上班,但不少人发现自己屋苑的大堂堆满从海里冲来的垃圾,倒下的大树树干有两三人围起来那么粗,主要干道严重瘫痪,铁路不通。这次自然灾害,是香港三十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切身的影响,诱发不少人反思人和自然之间的距离。
自然建筑在南涌出现的契机
朋友传来照片告知,香港的郊区受灾亦严重。在南涌,本来安置于鱼塘旁的货柜宿舍掉进塘里。另一处的货柜厨房被吹翻,导致形状扭曲,不能再用。还有更多农场的基建被破坏,需要重修。朋友问:“你可以帮手重建吗?”我知道南涌这个位于香港偏郊的地方,有一群人为着生态保育聚在一起,成立了活耕建养地协会(下称协会),及后朝着生态社区教育的方向努力营建。我提出:“你们会想用自然建筑的方式重建吗?”就这样,我走进南涌。但在这之前不无一番挣扎。
为何选择离开现代建筑
我是阿乐。建筑系毕业后到香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工作,开始了持续四年的规律:从市区的家出发,搭地铁,步行 5 分钟,到办公室的冷气房,开始 8 小时工作;下班以同样的路径回家。我最享受的或许是周末,因为可以到郊区行山。现在想来,为何我对每个周末都有如此强烈的渴望?不知会否有人跟我一样,往山林里跑,在大海中浮游,其实是在弥补生活中的某些匮乏。我想,如果是一条鱼,我会在大海里有怎样的一天?
我发现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很容易忘记在金鱼缸里的鱼,跟鱼塘里的鱼和大海里的鱼,本质上都是一条鱼。它们不是被观赏的鱼,不是被吃的鱼,它们是地球上的一员。
在工作的四年里,我尤其看到城市空间对这种共同性视觉的缺乏。市区的土地都插满高楼大厦,公共空间不足。在追崇高效的社会,空间都先让作功能性的使用。不说人要给车让行,而是要求容许其他生物共享这个空间,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我选择放下“以人为本”的视野,离开建筑公司,先学做一条鱼,摸索是否存在着一种容许各生命体共融地生活的人类建筑方式。
在外地遇上另类建筑的经验
到哪里寻找答案?离职后的一两年间,我去了多个地方,并觉察到我在建筑业所观察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根源。
在巴西,我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了当地政府的房屋部门。我被派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贫民窟,协助部门的公共空间设计工作。耗时三个星期在办公室做的公园设计草图拿到社区中心,迎来区内居民的回应竟是:“我们不需要公园,公共空间是犯罪活动的温床。”我察觉到这种建筑设计上的缺失。这种资本主导,从上而下的建筑过程,无法回应社区持分者的需要。而重大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建筑模式正主宰着很多地方的城市发展。
之后到印度的山区,我联同一个慈善团体为一个儿童之家改造厨房设施。该处的山区没有集中处理垃圾的系统,每个产生垃圾的单位都自行负责。如何负责?他们把垃圾拉到山边、路边、前院或后院露天燃烧。当中有大量不宜直接燃烧的物料,如包装纸、塑料等,一些对人体有害且让环境受损的气体就直接释放到大气中。大家都不以为意,现代的产品有太多是不可被循环或降解的。而鼓吹消费的发展模式,太容易使人忘记在过程中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不知不觉这种片面的价值观渗入世界各地文化。
接着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去了台湾参与团体“野地森活”的活动,协助建造一家用泥土做的小房子。第一眼看见这个正在建造的土房子,感觉不是特别壮观,又看不出有什么创新技术。参与过建造过程后我却被深深感动。土房子的建造不像现代建筑的建造。现代建筑建造地基的时候,不论建筑物规模,都会先把原本的泥土挖走,当工程废料送走,然后在土地上以混凝土封住,再在上面建一层又一层的楼房。土房子用的物料无毒无害,现代建筑的物料则经常有不少副产品产生:对环境和人体有害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刺鼻的强酸强碱等。土房子的建筑工地里,没有惯常见到的大型机械,或到处可见的危险物料。这种环境不期然使人放下警惕,容让来自更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人参与。台湾的朋友跟我说,这就是自然建筑。
在香港如何做自然建筑
自然建筑可以在香港发生吗?
自然建筑广泛的定义是指使用自然材料作为建材的建筑物。追求物料是在地的、低度加工、没有化学添加且可以逆转循环再生的。自然建筑同样关注人的维度,即重视在建造过程中,人与人(建造者与使用者)、人与自然所建立的关系。自然建筑运动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的回归土地运动( Back-to-the-Land Movement)所掀起,他们在没有建筑背景和资金的支持下,用在地的自然资源作为建筑材料,建立自己的居所。
在工作之前,我亲身去过南涌三四次。我对这地方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四小时往返市区的车程。直到一天,朋友传来电邮,说是邀请我参加南涌的市集,并附上照片一张。照片里是一片蓝天和一片绿意。远处的绿是山脊。山脚处点点白,似是一些小屋。前面的绿一时未认出来是什么,看见几个人在草堆里干活,应该就是一片还没长出禾的田。山和田之间也长满草,几乎看不出草是从水里长出来的。之后才知道那是芦苇。照片应该是初夏拍的,一片绿中隐约泛着夏日刺眼的白光。在电脑荧幕前看到这景象,好美。
没想到,自己由一位访客开始,接下了工作,到如今在村里生活。
工作开初,依然被南涌的自然环境和四时的景物所吸引。不时在劳累的工作过后,走到溪水里降温。南涌三面环山,水源充沛。涌口接连沙头角内海,海浪不大,岸边长满红树林。春夏的水很多,不少人长途跋涉从市区来,行溪涧看瀑布,看活跃于海岸、陆地和天空的昆虫等动物。秋冬留鸟和候鸟在溪边、海岸边觅食和停留,观鸟和生态爱好者经常流连。在城市长大的我,开始发现人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大。乡郊让我发觉,身边的环境有更多的物种存在,并以此为栖身之所。我要建筑的空间也许不只有人会光临。
人只是这片土地的其中一员。此刻承载着我们的土地,继承着过去的痕迹,亦将会是未来的资源。南涌自三百年前有客家人聚居,村落建于山脚,盆地用来种田种地。现在打开地图看,会发现鱼塘的面积比耕地要大得多。这个地貌的改变,源于1950-1960年间,田地被变更为更有经济价值的鱼塘。之后到了2000年代,一反香港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村中陆续有新的人口进驻。现在的南涌,常住的大概有五六十户。旧村民大多是退休年纪。活跃于村里的成员,有几户以不同生态友善模式种植的小农,还有做食物教育、身心灵活动的等等。
从2019年起,我以自然建筑的概念为基础,为这个新旧交融、背景多元的社区,尝试提出另类建筑的可能性。在过去两年多,我协助协会用泥土和竹建造了一个社区厨房,以及一个土窑。
厨房是协会每天都会用到的空间,成员普遍倾向以比较快的方法做一个临时厨房,并期望在未来的四五年间,协会的整体空间规划更为完整时,再另建正式的厨房替代这个临时厨房。南涌有什么在地的资源可作建筑用途?怎样的施工技术更易为一般民众所掌握?我记起香港有名的竹棚,不论是几十层高的大楼的维修棚,或是每逢盂兰节打醮的戏棚,都能在几天内完成。在南涌,鱼塘就在旁边,泥土容易获取,况且有朝一日厨房需要拆掉,泥土也可以直接回归土地而不污染环境。南涌的另一个鱼塘则被芦苇覆盖,可以善加利用,除了用作在地材料,也可以削弱芦苇的蔓延和生长速度。考虑到时间、在地资源、使用习惯后,我提出了一个方案:用搭棚的方式做厨房的结构,草挂在竹架上面,涂上泥土造成墙身,芦苇用作屋顶和檐篷。
厨房的方案只是个开端,之后的选材、施工和保养,是持续而反复的实验、验证和修正,有如各种生命必经的过程。自然建筑追求的,不是把自然物料直接应用而不作任何人为添加或改动。如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以类似的模式工作、运作或回应,我们就更像是一部机器,更不自然,不像我在自然中所见到的到处爬的番茄、会游会跳的野猪或会穿州过省的候鸟。对周遭环境及物种有更深入的理解,在建筑时使用适切的物料配合技术,是我所理解的自然建筑。竹的韧性可与钢材相比。不过竹糖分高,使用前要花点功夫:经过火烤,可以将里面的水分蒸发,养分变质,昆虫不爱;泥土是很好的隔热物,不过弊端是遇水会溶化变泥浆。石灰涂在泥土上则是天然的雨衣,石灰氧化后可以保护泥土减少雨水冲刷。
对从前的我来说,大自然是一幅美好的风景画;乡郊是个休闲、消遣或放下的后花园;而建筑是制造满足人类需求的空间。现在大自然的生物是我会去探望的对象,让我时刻学习其强大的生命力;村里的人是与我一起聚餐、工作、生活的人,是互相聆听和支持的伙伴;建筑是在建立容让更多生命互相交流、共生的环境。
参与者的反思
两年间,有超过100人次协助建造。土窑复修则有12个人参与连续8天的工作坊。这些参与者来自不同的背景:有退休的建筑师、学生、家庭主妇等,年龄则由18到65岁都有。
自然建筑需要身体老实的投入,即使这种劳动使人汗流浃背或肌肉酸痛,但依然有人持续地做。过去一年有一群大学生每月最少来参与一次自然建筑活动。什么驱使他们持续到来?他们的回答很单纯:“喜欢这里能放空,休息,能放下一些负担和压力。”面对世界的崩塌和失序,不少人都有种盼望,希望回到如常。一位参与者分享说她在南涌的山水、农田与各位的分享之间,找到一份天地自然之律可以遵循,使人感到心安。
我相信参与者能从这种身体经历中获得一种回报:接收来自自然的疗愈力量。不论是在处理竹枝或是调配泥土的时候,经常看见参与者对当下工作的沉醉。或许,过往太多的学习是在追求知性的收获,现在通过自然建筑能与自然接触,促发的是心灵的触动。这种触动,也许是反思和改变的起点。
触动使人意觉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人的关怀超越自我。曾经有一位土窑工作坊参加者反馈说,这种学习让她思考自己作为“人类”的身份,特别是自己在这地球上的角色。土窑完成后,另一位参与者反思:“那烧柴开窑烘面包会用上很多柴枝又释出很多气体,会不会是很不环保的行为?”觉察人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又意觉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改变的开始。带着这觉察检视现在的系统,那我们又是否知道电力所产生的污染都排放到哪里去了?要建造如此庞大的电力基建,又夷平了多少村落,影响了多少家庭?
我下潜到大海里,寻找我心中乐见的鱼儿。我看见有一些鱼的容身之所就在海草或珊瑚之间;鱼成群地觅食;鱼的食物来自其他的生物,而它产生的废物和排泄物又成为其他生物的养分。鱼的生命得以维持需要依靠互相贡献、互相成就、合作和支持。这是我在一条鱼身上学到的。人为生活所需而消耗和建造无可避免,但我们在获取自己所需的同时,是否可以多一份对其他生物的贡献?我希望人类的建筑方式可以朝向更为低生态负担的方向发展。参与自然建筑的活动也许是让自己保持着这一份生态观念的觉醒:人与各种生物互相依存。当更多的人保持这份觉醒,积极地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行动,我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就有改变的可能。
- 阿乐 自然建筑实践者与导师,定居于香港南涌附近的乡村,除了建筑,有时还会跳舞和做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