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索菲·班克斯
2006年,在伦敦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我,搬到了英格兰德文郡的美丽乡郊。因缘际会,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托特尼斯转型城镇项目,该项目後来拉开了全球转型运动的序幕。这个重新想像和塑造本地生活方式的运动刚启动几个月,就吸引了远在加拿大丶美国,意大利丶爱尔兰,乃至日本和巴西的伙伴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用我们发明的模式进行本地实践。这一切都让我倍感惊讶。在托特尼斯转型城镇项目成立1年後,我和伙伴协作了关於转型模式的第一次培训。又一年之後,我们将之推荐至世界其他国家。作为转型运动初创时期的主力军,我感觉自己就像站在风口浪尖上,既兴奋不已又感觉精力不济,因为成百上千的项目在积极探索,大家都渴望与我们联结丶向我们讨教,并分享各自的故事。
在伦敦的时候,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服务有精神疾病或创伤的人群。多年社区足球的经验让我有机会洞察,在自组织里大家如何共事共处,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人类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破坏的迟缓反应也引起我的注意,进而让我追问,这一切是如何与其他非故意而为之却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模式相关联的,此类模式在我所从事的心理学领域相当常见,无论是个人还是小组。搬到德文郡之後,我加入了当地一个专注於探讨人与人丶人与自然之平行关系的“生态心理学”小组。
依然记得第一次听罗布·霍普金斯分享转型理念时的感受,好像蓦然唤醒了内心深处沉睡多年的某些东西。从一个积极丶富有创意而让人真切向往的愿景出发,让大家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并激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真正的改变可以在本地发生,并启发其他社区去做相关的本地探索。在转型城镇项目的启动仪式上,有超过400人前来咨询并参与。那一刻我由衷地感恩,庆幸当时相信自己的直觉,给未知保留了充分的空间,让那些自己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得以降临和发生。
我与“生态心理学”小组的一位成员共同提议,在转型项目里设立一个专注於社区转化内在层面探索的小组。这个想法得到支持後,我们在市政厅组织了一次聚会,作为“心灵小组”的启动仪式。当时我们无法预计会有多少人来参加,可能寥寥无几,也可能济济一堂。最後实际来了50人,一位伙伴为此做了一个关於“生态心理学”的演讲。後来我们也与参与者一起探讨,一个关注社区转化内在层面的小组应该包含什麽内容。我们还邀请大家去想像,跟来自美好未来的人类去分享我们现处的时代,并描述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历史阶段活着的感受。我依稀记得,大家坐下来开始谈话的时候,有那麽一种触电的感觉,仿佛通过讲述想像的可能性,我们就已经在铺垫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

置身於转型运动核心10多年,我曾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各种转型实验小组共事。从中会发现,有些人很专注於转型的外在部分,包括为了获取可持续能源丶房屋和食物系统,以及恢复生态系统丶防止气候恶化等而采取具体行动。在我看来,从中映照出了西方的主流文化——注重经济发展丶就业和生产力,忽视身心健康和人际关系。有时被一群关心食物系统丶可再生能源或低碳建筑的人包围,我发现自己也很难去惦记内在转化的重要性。难道把所有的科技问题都解决了,一切就会变好吗?
之後回到心灵小组,我有机会听到大家分享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大家对於污染,对於原始森林或童年乐园被破坏的切身感受;对於气候异常的恐惧;对於近些年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的愤怒。有的人还会分享,自己倍感孤独,好像是家里或者公司唯一关心这些问题的人,看着身边大多数的人还在无止境地消费丶旅行和享乐,感觉自己近乎疯狂。我会发现,这些人因为有机会向他人诉说,建立起某种联结感和归属感,从而会获得很大程度的释怀和解脱。
有时我们会特别创造空间让大家去感受和表达,共同缅怀我们的悲痛,类似的空间在现代文化里日渐稀缺。我能分明感觉到,如果我们创造出一个时空让这一切能够安然发生,有利於将大家聚集在一起,建立一种深度的信任和联结。乔安娜·梅倩[1]的“重新联结的行动”(works that reconnects)以及新作《积极的希望》(active hope)当中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信息,帮助我们勇敢面对当下的混乱而不至於陷入癫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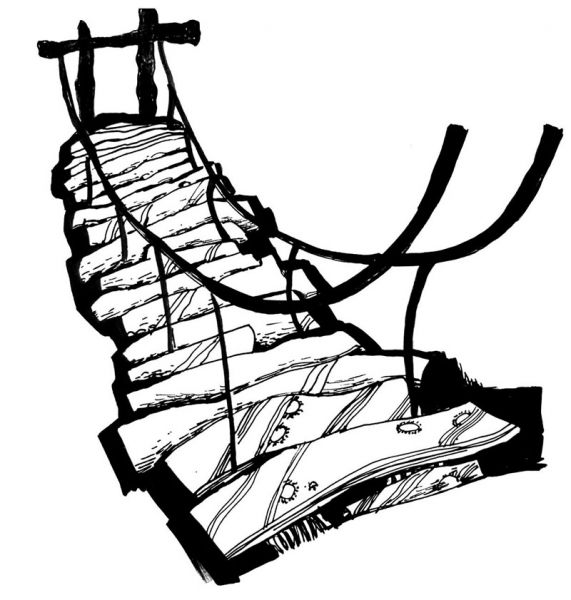
聚会时,我们会特别注重一起庆祝收获与进步,认可彼此的贡献,并肯定每个人为小组增添的缤纷色彩。有时候我们往往很容易陷入接踵而至的行动或任务而倍感压力,因而忽略了每个人的付出。
我们也会建立支持互助体系,例如,家园小组——让邻里可以相聚在一起,倾诉内在的感受,或者分享一些节约能源丶减省开支的技巧;也会为肩负重任的一线行动者提供免费的指导和协助。
心灵小组还会组织季节性的庆祝,感恩大自然的美丽和富足,让我们因之而存在。也会与大家分享关於内在转化的教育,并将之与组建小组的过程结合起来,一起展望和创造新的方式,同时也尊重和肯定旧的路径,将二者融会贯通至各种有趣的日常活动,包括一起种植和加工食物丶手作劳动,以及分享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发现许多原本对内在转型毫无兴趣的人也开始觉知,一味专注於操作层面容易让人陷入困境。很多个人和团体在开始时饱含能量和热情,但几年後就感觉疲惫不堪。很多参加我的培训的伙伴分享说,筋疲力尽是很多自然保育工作者的通病。据我所知,在许多环境保护组织中,人们往往会因为热情和执着而不计後果地付出,最後心力交瘁,有些人甚至因此而病倒,或者因为免疫系统受损而长期处於某种衰竭状态。这似乎成了一个悖论,一个以可持续性为核心目标的运动,却创造出一种对许多个体而言都不可持续的文化,大家正在通过透支自己的方式来阻止地球资源被透支。
这不禁让我反思,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行动与休憩丶外在与内在丶任务与关系等的各种矛盾与失衡。有时候会惊异地发现,在群体中,包括我参与其中的小组,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是那些专注於“做”的人和那些关心“存在”的人之间的张力。
我注意到,在许多转型小组中,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事情上,包括活动丶项目丶社区行动等,却很少关心大家的身心状态。无形中就造成了某种韧性缺失——大家可能已经接近崩溃但却毫不觉察,加上文化又总是强调坚不可摧才是好的,而坦承自己在挣扎则不会被接受。因为恐惧失败和无能为力,加上全球生态形势严峻所造成的迫在眉睫的压力,都在持续强化“我们不能停下来”的感受以及不断付出的意愿。如此的付出,精神可嘉,却以伤害自己为代价。
2007年3月,心灵小组为托特尼斯转型项目第二次核心小组会议设计了“个人可持续性检查”,这是我们早期对该项目的贡献之一。当时,我们带领不同主题小组的7位成员,轮流回答了两个问题:第一,作为志愿者,我们在项目中的付出和收获是什麽?第二,保持当前状态,我们还可以继续多久?
我们发现,没有人认为自己可以维持现有的投入程度超过6个月甚至1年。在这麽热情高涨的时刻,这可是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由此我们意识到,必须马上做出一些调整,否则项目很快就做不下去,只剩下一些疲惫不堪的人员。对此我们决定,要不寻求资金雇用一名工作人员,不然就缩减规模。後来我们幸运地找到资助,雇用一名兼职项目人员,让项目得以乘势继续往前推进。
之前我曾听说有一个团队,在社区行动2年後筋疲力尽,随後,花了1年的时间纯粹用於深入认识彼此。我由衷地为他们如此明智的决定而高兴。那年年底再见时,他们又神采飞扬了。
一位转型老师曾分享两项非常有用的研究成果,这成了我最喜欢的统计数字:
统计1 日常工作中,为了让团队保持愉悦,正面的言辞与负面的言辞比例需要在5:1以上,换言之,每1个批评或抱怨需要5个支持或称赞来抵消。据我所知,人际关系中也有相关的研究,比例相近,对於真正幸福的夫妻而言,二者比例高达20:1。
统计2 投入25%以上的时间钻研合作方式的团队工作效率最高,主要包括文化丶沟通丶互相认识丶建立信任丶澄清目标丶角色和决策程序等。在这些方面投入时间少於25%的团队,开始时好像事半功倍,但长远而言往往会因为明晰不足和信任缺失而付出更大代价。
我欣喜地看到,10多年前不被关注的身心交瘁问题,如今引起了很多英国行动者的关注,大家不仅关心外在行动,也会注重照顾好自己和彼此,建立滋养和支持性的团队文化。在我们自身的转型运动中创造健康文化成了大家的重要焦点。
深感荣幸自己有机会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话转型,特别是关於内在转型。它拓宽了我对当下各种挑战的认知,也因此清楚我们正在制造的问题,不仅存在於外部空间,也存在於内在世界。我还没去过中国内地,但有幸曾被邀请到香港与一群关注转型的伙伴共事,他们当中有的关注影响子孙後代的自然保育,有的关注社区生活的重建,以让更多的人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并拥有更强的归属感和联结感。
在香港我曾遇到一些人,倾尽心血去追问社区的本质与内涵——工作压力巨大但还依然探索相处的学问,并尝试开展与食物丶住房丶抚养孩子相关的经营。他们对群体生活的三个维度,包括结构丶关系和拼搏,都有透彻的洞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
上次访港期间,我与来自世界各地正在经历不同工业化阶段的人们展开了一次共同的探索。在我看来,起源於西方的工业文化可以创造很多的美好,但也能给自然界和人类及其社区带来极大的伤害。在西方,我们已经走到工业化尽头,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在能源和资源使用丶二氧化碳排放,以及赖以生存的生命网等方面,我们都在挑战地球的极限。中国正在快速地推进工业化,英国花了几百年而中国仅用了几十年。
虽然低碳未来是唯一的出路,但要让人们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那些掌握着财富和权力的人早已习惯於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并视之为一种身份和需要,而不觉得奢侈。在英国,我们经历过多年的“经济紧缩”,这一制度要求大部分人节俭生活,但富人却因此而更富有,生活更奢侈。这是降低能源使用的一种方法,却也造成非常不公平的後果,最终制造出巨大的痛苦和不安,因为我们是对不公平极度敏感的生物。转型鼓励我们去展望的另一条道路,是去想像一个所有人都能各取所需的世界,习惯了奢侈生活的人也会大大降低其消耗。这会给不同的国家带来不同的影响,取决於其消费水平和科技程度,对富人的影响也更大。
我一直认为,转型与我们这些生活在高度工业化国家的人最相关,尤其是当中的富裕阶层。转型的最初原型是关於降低能源使用的方法——消耗最多的人学习如何减少耗能。但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丶和平丶包容的未来,让所有人都感受到富足丶价值丶能量丶安全和联结,就需要我们一起去想像未来可能的样子,并为之实现而付出努力。工业化只让一小撮人获益,却伤害了很多人,并影响了每一个人乃至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在这个跌宕的年代,我们如同一个物种集体去应对工业化的後果,其中最有效的是去发挥我们的想像力。
当下,故事丶电影和媒体正大肆渲染一个充满技术战争丶灾难和绝望的未来。与此相对,有一种更友爱且造福众生的行动,那就是去想像,我们倾尽所能最终扭转乾坤,50年或100年之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地球生态获得呵护和修复,反过来又滋养人类生活。如此一来,我们的社区丶国家丶世界会是什麽样子呢?在自己生活的地方,走在街上会是什麽样子?食物的味道丶空气的气息丶伴随清晨醒来和晚上入睡的声音是什麽?你和其他人是怎样度过每一天的?老人和孩子们在哪里?他们正在教和学什麽?
我同意许多人的观点,这是一个过去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时代,一切都更加脆弱,也更大程度依赖於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行动。这是现实,却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既有巨大的伤害,也有伟大的疗愈。我坚信,我们有能力构建出深度信任丶坚持不懈的团队,致力於为众生福祉而共同努力,这是创造一个我们真正向往的未来的关键所在。
索菲·班克斯 Sophy Banks
英国托特尼斯转型项目“内在转化小组”发起人
翻译:梁 迎 梁笑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