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木兰
我是河南开封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子。很多人会脱口叫我“木兰”,是因为一时想不起我的名字,我不介意,很喜欢“木兰”这个称呼,因我和木兰几乎分隔不开。木兰 2010 年刚成立时,我就吃、住、睡在木兰的任何一个活动中心之中,生活和工作完全不分。我和木兰几乎融为一体,无论是从外界传播,还是从我自己的时间、精力的投入而言,都是如此。
我只是木兰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我们 4 位女性一起创办了木兰花开,张睿、张春芬、赵忆帆和我,几乎是一拍即合,都身为流动女性,更能感同身受基层女性的弱势地位和面临的困境。
我们咨询了很多朋友,自己也想了很多名字,最后机构定名为“木兰花开”,是因为我们把“花木兰”和流动女性做了一个比较,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第一,都是女性身份;第二,都是远离家乡;第三,都是为了支持家庭,花木兰是替父顶弟从军,一个一个的流动姐妹是为了减轻家里经济压力,甚至是为了支持哥哥、弟弟们读书,成了家庭的经济支柱;第四,都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姐妹们的劳动汇聚在一起,为了国家的 GDP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是常常不被看见。当然也不能完全类比,我们也找出了不同的地方,比如,我们很多姐妹多是被迫做了这样的选择,不像花木兰那样积极主动;花木兰很自信,有很强大的自我,我们的姐妹很多人没有“自我”,那个小小的“自我”常常被忽略,连自己都看不见;花木兰的贡献被看见,被传颂,流动姐妹的劳动却常常不被看见。

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众多的流动姐妹是非常相似的,可以说我既是其中的一员,又是典型的代表。我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所幸父母重男轻女思想不是特别严重,就有幸多读了几年书,没有像同龄的女娃那样早早地嫁人生子。有机会离开农村,走到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中去,让我的人生变得厚重:当过老师,做过小生意,南下寻梦的几年,青春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疾飞。
在工厂流水线做普通工人的时候,我感觉到生命是那么的黑暗,找不到生存的意义,用青春、汗水、健康、骨肉分离换来薄薄的几张钞票,仅够维持生计,连生病都生不起。长长的流水线上, 充满着流动女工的血泪和绝望,困住了一个一个青春少女。我自己是一名曾留守而现在处于流动状态的妇女。同样我的女儿也有过留守和流动的经历。我们都将各自的伤痛埋在心底,几乎从来不正面谈起。在她留守的日子里,每次看到一家人走在一起,我的眼光会跟着人家走很远;当年,每次听到看到有像女儿大小的孩子哭泣,我会忍不住红了眼眶。
因为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和个人的生命历程,其他的姐妹也有相差不太大的背景,所以“木兰花开”从诞生之初,它的定位,它的价值观,就有其内生的基因,诸如以人为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争取外部平等、推动性别平等、践行内部平等民主、看见每个人、以优势视角发挥每个人的力量等。
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我们在很贫瘠的土壤中发芽。我们最初选定的社区在北京五环外,临近五号线终点站的东三旗,对面不到一千米就是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东三旗是一个外来人口聚集很密的城边村,据说当时人口约 3 万人。在村东南有一大片区域,是废品收购站,很集中的一片地上以“家庭”为主的一个个收购站,搭着简易的棚屋,人们就生活在废品和垃圾之中。这片土地的上空,经常弥漫着不同的味道和烟雾。人们就在这里生活工作,孩子们就在废品堆中淘宝、玩耍、长大。我们的活动室就设立在这片收购废品区域的边缘,在一个小二层楼的楼上,二房东是做饭店的。这二楼由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和两个10平方米左右的包间组成。我们就选了其中一个包间做办公室,另外一个包间做集体宿舍,经常四五个人挤在那个小房间里,连转身都不方便。厕所在500米外的废品收购站区域内,上厕所之困难竟成了那一阶段考验我们和前来做志愿者的学生的一大挑战——能顺利上厕所,才有可能留下来。
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要为基层流动女性做些事情,我们找到了大家居住的地方,也做了调研,了解了大家的基本状况。那我们就要和她们在一起,来看看我们做些什么事情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成立之初的那段日子异常艰辛。刚刚半年,机构就面临着生存挑战,没有任何资助了。我们是各奔前程,还是继续坚持?经过一个会议讨论,最后几位伙伴不约而同做出了决定:留下来,一起面对挑战。用春芬的话就是“只要有馒头吃,我们就要做下去”!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长达一年左右的吃“馒头大餐”,睡“贵宾桌”(把桌子拼起来当床)、“贵宾地”(打地铺)的日子。当时大家愿意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认为我们所选择的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和跟我们情况差不多的姐妹在一起,我们不仅仅满足了她们的某些需求,我们也得到了滋养,这个过程是相互的。跟我们在一起的姐妹和孩子,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关系,有什么困难会和我们一起讨论,甚至把特别难堪的困境讲述出来,我们一起抱头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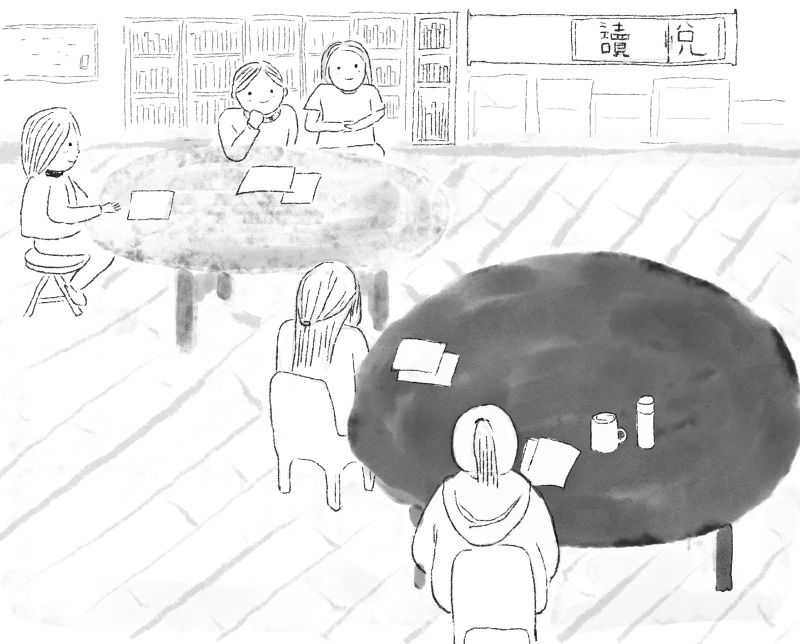
我们在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做我们认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社区姐妹精神文化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成立文艺队,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这些歌舞的内容都和大家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很多姐妹们听了我们的歌,好像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加入了我们就有了归宿感,好像在北京有一个“娘家”。另外一类事情就是社区姐妹最关心的孩子教育问题,我们组织志愿者,做四点半课堂、一对一成长陪伴等,让孩子们得到支持和陪伴,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区姐妹的压力。另外就是维持机构运作的二手物品义卖,大家捐赠过来的物资,以衣物为主,我们在社区里进行义卖,倡导绿色消费,减少物资的浪费,也减轻了大家的经济负担,同时支持我们继续向前。我们真的就像一棵野生土长的小草,有点水就能活,给点阳光就灿烂。凭着对我们所做事情的认同,我们坚持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慢慢地越来越有起色。
2015年的时候,机构陷入了一个瓶颈期。有内部问题,大家前期投入太多,没有上下班概念,经常没有时间休息,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又看不到工作成效。我们慢慢地感觉到了迷茫,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外部也充斥着各种对公益的论述。最刺激我们的就是所谓“老小树”,意思是机构成立了好几年还发展不起来。对号入座,我感觉“木兰”就像是一棵长不大的树,甚至还不能说长成了树, 我们还是一棵在艰难生长的小草。随时一个危机,就可能让这棵小草活不下去。
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虑,经常失眠上火,见人的时候,常常满嘴火泡儿,一个正在长起,另外一个刚刚结痂,被凛冽的北风一吹,一张嘴就裂开,血就渗出。自己又强撑着,不肯也不知向谁说,偶遇朋友关心问候,就会突然红了眼眶,不敢和人对视,不敢把脆弱的一面给人看见。当时的我在个人生活中也像陷在泥沼里的女人,困在婚姻中找不到自我;有过丧偶式育儿的苦闷,苦苦挣扎着寻找爱和出路。我努力思考我的人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尝试用各种方式去改变自己,改善夫妻关系……在苦闷中挣扎,深深地陷入了自我否定,一点也找不到自己的成就感和长处,甚至觉得活着的自己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任何价值。那段时间,是我人生至暗的阶段,像是永远都走在漫长的无光隧道里,时间像是永远都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个人层面,好在有众多朋友以各种方式陪伴着我,有长长的电话,有相拥而泣的共情,有持续不断的支持,有……最终,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历程,我结束了近20年的婚姻。自由需要争取,也是需要适应的,只能慢慢地从泥泞中拔出腿来,一步一步向前迈。最终我发现,一个人的日子也可以充满快乐、自主、自由!
机构层面,与社区伙伴及其他合作方建立起新的合作,像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剂。我们看到每个个体的力量,也看到每个组织的不同。我们就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陪伴着我们社区姐妹。当把心态放慢下来,人就不再那么浮躁,反而有可能给到社区的姐妹们更多的支持和看到更多可能性。接着,我们在机构的工作上也做了调整,放弃大而全机构的预期,根据现实的条件和人手做了一定程度的精简。比如,我们停止了社区二手店的运营,也减少了一部分儿童活动。我们找回自己的初心,把深度陪伴、促进姐妹成长和发声作为我们工作的核心。我们同事慢慢认可木兰的“小而美”,我虽然不能认同,但也不再自我对号入座“老小树”的评判,甚至觉得我们本身就是一棵倔强野草,自有草生存的价值。我们不是参天大树,那就好好地做一棵“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吧!
我们就这样彼此扶持着,慢慢前行。我们团队陪伴社区姐妹,也在陪伴彼此中互相汲取力量,一起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挑战,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这些年,我们的姐妹因为家庭原因或外部压力,有的离开了北京回到家乡,有的去了别的城市,还有一些留在社区,继续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慢慢接纳了这种“流动”状态,因为“在一起”,并不以物理空间为限定。
姐妹们的成长最初以关注孩子为主,在我们的引导和陪伴下,也开始关注自我的发展。我们以发生在自己身上真实的事情,在外部的支持下排演了一部《生育纪事》来讲述基层女性的生育困境,让姐妹们经历过的苦难与艰辛可以表达和被看到,甚至让这个话题被公共关注和讨论。通过讲述,也让我们姐妹们有机会得到疗愈。此外,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手作坊,妈妈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一起做手工牛轧糖、雪花酥等,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不一样的生活,相信劳动对于生活的价值。手作坊虽然只是一个小的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里的劳动者和管理者,这是属于我们的空间。记得刚开始时,姐妹们不习惯开会讨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当我们慢慢推动,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和想法之后,大家也慢慢地愿意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个过程其实既是赋权赋能的过程,也是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在这里,每个姐妹都有了成长的机会,不再是工具异化的人,而是身心与精神都独立且完整的个体。

木兰从不知道能存活多久,到不知不觉中走过了10年,我们以自己的步调,走我们自己的路。回望来时路,有感慨有泪滴,是经历也是沉淀。我们熬过了疫情,进入到了后疫情时期,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我们团队的整体心态从容了很多,仿佛人和机构都到了一个成年期,不再那么惧怕变化和未知。即使面对压力,也心知肚明无可逃避,只能面对,所以倒也坦然了许多。我们不再怕机构“死亡”,选择向死而生,就能从容地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做公益的十几年里,有挫折,有困顿,至今依然踌躇前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木兰的本命年,木兰12岁了,我48岁了。回望这有晴有雨的48载,感谢生命,也感谢相遇的每一个人。路漫漫其修远,前路仍有浓雾有坎坷……看清生活的真相,还依然热爱生活是一种勇气。我选择活在当下,无愧当下,尽心尽力做好每件事,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木兰选择向死而生,努力活成一种绽放的姿态,是小草也好,是野花也罢。我们不追求高大上,就认真平凡地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和我们社区姐妹一路同行,一起面对未来的坎坷路途与更多的不确定。
- 木兰 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创始人之一、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