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木蘭
我是河南開封人,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女子。很多人會脫口叫我「木蘭」,是因為一時想不起我的名字,我不介意,很喜歡「木蘭」這個稱呼,因我和木蘭幾乎分隔不開。木蘭2010年剛成立時,我就吃、住、睡在木蘭的任何一個活動中心之中,生活和工作完全不分。我和木蘭幾乎融為一體,無論是從外界傳播,還是從我自己的時間、精力的投入而言,都是如此。
我只是木蘭的創始人之一,當時我們4位女性一起創辦了木蘭花開,張睿、張春芬、趙憶帆和我,幾乎是一拍即合,都身為流動女性,更能感同身受基層女性的弱勢地位和面臨的困境。
我們諮詢了很多朋友,自己也想了很多名字,最後機構定名為「木蘭花開」,是因為我們把「花木蘭」和流動女性做了一個比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第一,都是女性身份;第二,都是遠離家鄉;第三,都是為了支持家庭,花木蘭是替父頂弟從軍,一個一個的流動姐妹是為了減輕家裏經濟壓力,甚至是為了支持哥哥、弟弟們讀書,成了家庭的經濟支柱;第四,都為國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些姐妹們的勞動匯聚在一起,為了國家的GDP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只是常常不被看見。當然也不能完全類比,我們也找出了不同的地方,比如,我們很多姐妹多是被迫做了這樣的選擇,不像花木蘭那樣積極主動;花木蘭很自信,有很強大的自我,我們的姐妹很多人沒有「自我」,那個小小的「自我」常常被忽略,連自己都看不見;花木蘭的貢獻被看見,被傳頌,流動姐妹的勞動卻常常不被看見。

我自己的個人經歷和眾多的流動姐妹是非常相似的,可以說我既是其中的一員,又是典型的代表。我生長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所幸父母重男輕女思想不是特別嚴重,就有幸多讀了幾年書,沒有像同齡的女娃那樣早早地嫁人生子。有機會離開農村,走到更廣闊更精彩的世界中去,讓我的人生變得厚重:當過老師,做過小生意,南下尋夢的幾年,青春在工廠的流水線上疾飛。
在工廠流水線做普通工人的時候,我感覺到生命是那麼的黑暗,找不到生存的意義,用青春、汗水、健康、骨肉分離換來薄薄的幾張鈔票,僅夠維持生計,連生病都生不起。長長的流水線上,充滿著流動女工的血淚和絕望,困住了一個一個青春少女。我自己是一名曾經留守而現在處於流動狀態的婦女。同樣我的女兒也有過留守和流動的經歷。我們都將各自的傷痛埋在心底,幾乎從來不正面談起。在她留守的日子裏,每次看到一家人走在一起,我的眼光會跟著人家走很遠;當年,每次聽到看到有像女兒大小的孩子哭泣,我會忍不住紅了眼眶。
因為有這樣的親身經歷和個人的生命歷程,其他的姐妹也有相差不太大的背景,所以「木蘭花開」從誕生之初,它的定位,它的價值觀,就有其內生的基因,諸如以人為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爭取外部平等、推動性別平等、踐行內部平等民主、看見每個人、以優勢視角發揮每個人的力量等。
就像一棵小草一樣,我們在很貧瘠的土壤中發芽。我們最初選定的社區在北京五環外,臨近五號線終點站的東三旗,對面不到一千米就是號稱「亞洲最大社區」的天通苑。東三旗是一個外來人口聚集很密的城邊村,據說當時人口約3萬人。在村東南有一大片區域,是廢品收購站,很集中的一片地上以「家庭」為主的一個個收購站,搭著簡易的棚屋,人們就生活在廢品和垃圾之中。這片土地的上空,經常彌漫著不同的味道和煙霧。人們就在這裏生活工作,孩子們就在廢品堆中淘寶、玩耍、長大。我們的活動室就設立在這片收購廢品區域的邊緣,在一個小二層樓的樓上,二房東是做飯店的。這二樓由一個30平方米左右的大廳和兩個10平方米左右的包間組成。我們就選了其中一個包間做辦公室,另外一個包間做集體宿舍,經常四五個人擠在那個小房間裏,連轉身都不方便。廁所在500米外的廢品收購站區域內,上廁所之困難竟成了那一階段考驗我們和前來做志願者的學生的一大挑戰——能順利上廁所,才有可能留下來。
我們最初的想法,就是要為基層流動女性做些事情,我們找到了大家居住的地方,也做了調研,了解了大家的基本狀況。那我們就要和她們在一起,來看看我們做些什麼事情能滿足大家的需求。成立之初的那段日子異常艱辛。剛剛半年,機構就面臨著生存挑戰,沒有任何資助了。我們是各奔前程,還是繼續堅持?經過一個會議討論,最後幾位伙伴不約而同做出了決定:留下來,一起面對挑戰。用春芬的話就是「只要有饅頭吃,我們就要做下去」!之後我們就開始了長達一年左右的吃「饅頭大餐」,睡「貴賓桌」(把桌子拼起來當床)、「貴賓地」(打地鋪)的日子。當時大家願意堅持下來,是因為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認為我們所選擇的是非常有價值和意義的事情,和跟我們情況差不多的姐妹在一起,我們不僅僅滿足了她們的某些需求,我們也得到了滋養,這個過程是相互的。跟我們在一起的姐妹和孩子,已經和我們建立了很深的信任關係,有什麼困難會和我們一起討論,甚至把特別難堪的困境講述出來,我們一起抱頭痛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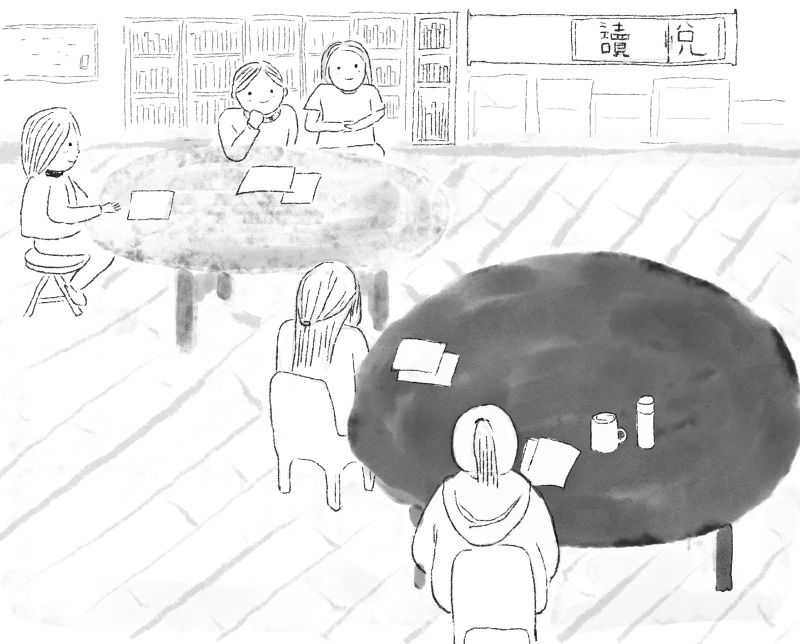
我們在幾乎沒有任何支持的情況下,繼續做我們認定的事情。這些事情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社區姐妹精神文化的支持和陪伴,我們成立文藝隊,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這些歌舞的內容都和大家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很多姐妹們聽了我們的歌,好像找到了另外一個自己,加入了我們就有了歸屬感,好像在北京有一個「娘家」。另外一類事情就是社區姐妹最關心的孩子教育問題,我們組織志願者,做四點半課堂、一對一成長陪伴等,讓孩子們得到支持和陪伴,間接地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社區姐妹的壓力。另外就是維持機構運作的二手物品義賣,大家捐贈過來的物資,以衣物為主,我們在社區裏進行義賣,宣導綠色消費,減少物資的浪費,也減輕了大家的經濟負擔,同時支持我們繼續向前。我們真的就像一棵野生土長的小草,有點水就能活,給點陽光就燦爛。憑著對我們所做事情的認同,我們堅持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慢慢地越來越有起色。
2015年的時候,機構陷入了一個瓶頸期。有內部問題,大家前期投入太多,沒有上下班概念,經常沒有時間休息,做的事情越來越多,好像永遠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又看不到工作成效。我們慢慢地感覺到了迷茫,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外部也充斥著各種對公益的論述。最刺激我們的就是所謂「老小樹」,意思是機構成立了好幾年還發展不起來。對號入座,我感覺「木蘭」就像是一棵長不大的樹,甚至還不能說長成了樹,我們還是一棵在艱難生長的小草。隨時一個危機,就可能讓這棵小草活不下去。
那段時間我特別焦慮,經常失眠上火,見人的時候,常常滿嘴火泡兒,一個正在長起,另外一個剛剛結痂,被凜冽的北風一吹,一張嘴就裂開,血就滲出。自己又強撐著,不肯也不知向誰說,偶遇朋友關心問候,就會突然紅了眼眶,不敢和人對視,不敢把脆弱的一面給人看見。當時的我在個人生活中也像陷在泥沼裏的女人,困在婚姻中找不到自我;有過喪偶式育兒的苦悶,苦苦掙扎著尋找愛和出路。我努力思考我的人生到底哪裏出了問題,嘗試用各種方式去改變自己,改善夫妻關係......在苦悶中掙扎,深深地陷入了自我否定,一點也找不到自己的成就感和長處,甚至覺得活著的自己像是行屍走肉,沒有任何價值。那段時間,是我人生至暗的階段,像是永遠都走在漫長的無光隧道裏,時間像是永遠都處於黎明前的黑暗。
個人層面,好在有眾多朋友以各種方式陪伴著我,有長長的電話,有相擁而泣的共情,有持續不斷的支持,有......最終,經歷了一番艱難的歷程,我結束了近20年的婚姻。自由需要爭取,也是需要適應的,只能慢慢地從泥濘中拔出腿來,一步一步向前邁。最終我發現,一個人的日子也可以充滿快樂、自主、自由!
機構層面,與社區伙伴及其他合作方建立起新的合作,像是給我們打了一支強心劑。我們看到每個個體的力量,也看到每個組織的不同。我們就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陪伴著我們社區姐妹。當把心態放慢下來,人就不再那麼浮躁,反而有可能給到社區的姐妹們更多的支持和看到更多可能性。接著,我們在機構的工作上也做了調整,放棄大而全機構的預期,根據現實的條件和人手做了一定程度的精簡。比如,我們停止了社區二手店的運營,也減少了一部分兒童活動。我們找回自己的初心,把深度陪伴、促進姐妹成長和發聲作為我們工作的核心。我們同事慢慢認可木蘭的「小而美」,我雖然不能認同,但也不再自我對號入座「老小樹」的評判,甚至覺得我們本身就是一棵倔強野草,自有草生存的價值。我們不是參天大樹,那就好好地做一棵「春風吹又生」的野草吧!
我們就這樣彼此扶持著,慢慢前行。我們團隊陪伴社區姐妹,也在陪伴彼此中互相汲取力量,一起面對生活和工作的挑戰,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這些年,我們的姐妹因為家庭原因或外部壓力,有的離開了北京回到家鄉,有的去了別的城市,還有一些留在社區,繼續跟我們在一起。我們也慢慢接納了這種「流動」狀態,因為「在一起」,並不以物理空間為限定。
姐妹們的成長最初以關注孩子為主,在我們的引導和陪伴下,也開始關注自我的發展。我們以發生在自己身上真實的事情,在外部的支持下排演了一部《生育紀事》來講述基層女性的生育困境,讓姐妹們經歷過的苦難與艱辛可以表達和被看到,甚至讓這個話題被公共關注和討論。通過講述,也讓我們姐妹們有機會得到療癒。此外,我們也成立了自己的手作坊,媽媽們發揮自己的特長,一起做手工牛軋糖、雪花酥等,用我們的雙手去創造不一樣的生活,相信勞動對於生活的價值。手作坊雖然只是一個小的團體,但我們每個人都是這裏的勞動者和管理者,這是屬於我們的空間。記得剛開始時,姐妹們不習慣開會討論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當我們慢慢推動,尊重每個人的意見和想法之後,大家也慢慢地願意坦誠地說出自己的想法。這個過程其實既是賦權賦能的過程,也是每個人成長的過程。在這裏,每個姐妹都有了成長的機會,不再是工具異化的人,而是身心與精神都獨立且完整的個體。

木蘭從不知道能存活多久,到不知不覺中走過了10年,我們以自己的步調,走我們自己的路。回望來時路,有感慨有淚滴,是經歷也是沉澱。我們熬過了疫情,進入到了後疫情時期,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和質疑。但是我們團隊的整體心態從容了很多,彷彿人和機構都到了一個成年期,不再那麼懼怕變化和未知。即使面對壓力,也心知肚明無可逃避,只能面對,所以倒也坦然了許多。我們不再怕機構「死亡」,選擇向死而生,就能從容地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做公益的十幾年裏,有挫折,有困頓,至今依然躊躇前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木蘭的本命年,木蘭12歲了,我48歲了。回望這有晴有雨的48載,感謝生命,也感謝相遇的每一個人。路漫漫其修遠,前路仍有濃霧有坎坷......看清生活的真相,還依然熱愛生活是一種勇氣。我選擇活在當下,無愧當下,盡心盡力做好每件事,努力工作,認真生活。木蘭選擇向死而生,努力活成一種綻放的姿態,是小草也好,是野花也罷。我們不追求高大上,就認真平凡地做我們能做的事情,和我們社區姐妹一路同行,一起面對未來的坎坷路途與更多的不確定。
- 木蘭 北京木蘭花開社工服務中心創始人之一、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