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龍集文 陳韋帆 整理 | 龍集文
隨著鄉村振興政策的逐步深入,越來越多的社會工作者作為政府、企業、基金會等各方資源和力量的「中介者」進入到鄉村工作當中,開拓了新的局面,也面臨諸多工作與生活的挑戰。2023年年初,社區伙伴農村團隊同事陳韋帆與長期紮根西南地區村寨的社工伙伴龍集文,就「社工的鄉村工作與生活」進行了對話。感謝龍集文的整理與分享——
我眼中的鄉村社工:攪動與漣漪
你是如何理解鄉村社工的?據你了解,鄉村社工的日常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我理解的鄉村社工應該熱愛鄉村,了解鄉村面臨的挑戰,並願意與村民一起應對挑戰。
每次去到一個新的村莊開展駐村工作,開始進入時總會受到很多感官上的衝擊,對村裏的人文自然都充滿好奇,而村民也會對社工產生好奇——「你們是來幹什麼的?來自哪裏的(哪個單位、哪裏的人)?」
初始進入村莊是最「躁動」的階段,還不知道自己這顆石頭會落到哪個位置上。在村裏待久了,沉到自己的位置,才能感受到更多村裏的人情世故、過往今來。
說到日常狀態,記得我最開始在重慶的鄉村駐村時,每天都在思考怎麼完成項目的走訪任務、個案服務和小組活動,怎麼組織院壩活動等等。那時候我並沒有怎麼去感受或發現村民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的,需要什麼樣的「支持」。現在回想起來很遺憾,因為那個村子有很好的村民自組織「老年協會」,又得到政府、社區和村民多方認可,骨幹們幹勁十足,但是我卻很少思考如何支持他們的工作,只想著怎樣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到第二個村莊駐村時,在村裏做個案、開小組時我有種無力的感覺——個案、小組和活動,真的可以解決鄉村的各種「問題」嗎?村莊的需求到底是什麼?他們真的需要外來人的服務嗎?想起曾駐點的一個村,有一位村民本身很有影響力,他家庭院是村民開會聚會的地方。我們開展服務後發現這一點,經常支持他經費,請他召集大家聚會開會。但時間一長卻發現,沒有經費提供時,他或者村民就不主動聚會了。另外,在社工經常承擔的困境人群個案救助工作中我也觀察到,社區本身對老人、殘障群體是有一些支持的,鄰里親戚的照顧也很多,但社工服務介入後,有時就會讓社區原有的照顧減少,甚至引起其他村民的妒忌。
為此,我開始從鄉村本身的倫理關係角度審視自己的行動。在我看來,社工作為外部的力量進入鄉村提供公共服務,有時候可能反而是一種「破壞」——對村莊本身互助系統、社群關係的破壞。
在個案服務中我會發現,在村子裏進行個案和小組服務,根本無法按社會工作教材中的方法來做,脫離實際的方法經常讓我找不到適切的落腳點,不僅痛苦,而且還會對社工這個行業和自己產生很多懷疑。我開始逐漸認識到,村裏本有互助傳統,其實並不太需要社會工作這種外來的協助,當我作為社工企圖去解決問題時,原本發揮作用的機制可能會因為外部力量的介入反而「失靈」,社工帶到村裏的外部影響,特別是負面的影響,讓當時的我非常糾結甚至害怕去行動。
如今,回到當下的日常狀態,最大的改變是我不再糾結自己到底掌握多少社工服務技巧,而更看重自己能了解多少村裏的事情,能感受多少村民的情緒,如何通過對話了解村民真實的想法,然後思考自己能和大家一起做什麼,並和大家一起探討這些做法是否能給大家帶來比較好的反饋,是否能通過正向反饋來推動村民更積極的行動。為此,鄉村社工就像一顆不屬於這個水塘的小石頭,但又真實地留在這個水塘裏,感受這裏的漩渦、水流、漣漪等等。雖然石頭不會動,但我們可以影響身邊的人,可以和大家一起做些事情。雖然我們只是小石頭,但也是生態的一部分,也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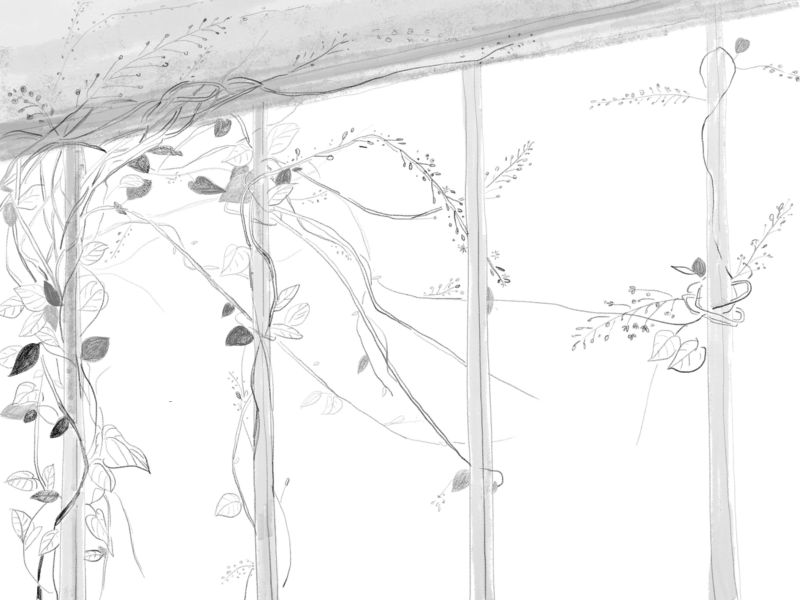
過程中的我:一顆「石頭」對自己存在的覺知
根據過往的體驗,你覺得有哪些時刻或事件豐富了你對鄉村社工的理解和想像?
有很多,其中包括參加一個在貴州舉辦的鄉村工作研習營。參加研習營看似個很偶然的機會,但卻是我走這條路的一個必然節點,一個必經之地。參加研習營之前,我只從一個社工、一個工作者的視角來看待鄉村的項目服務。對於活動和服務的設計及其意義的思考也局限在項目裏,即便心裏會想是不是可以更「多」、更「好」一點,但不知道怎樣去思考與領悟什麼是「多」和「好」。研習營之後,協作者培養計劃啟發了我,追求「多」和「好」之前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社區工作,理解社區發展、變化的脈絡,深思「文化反思」對鄉村工作的意義。
聽起來,你對鄉村社工的想像也是一個逐步打開的過程,一路走來,當中哪些人給你帶來新的啟發?
很多同行和前輩的實踐經歷,以及自己實踐過程中遇到的困難,都會慢慢積累和深化我對鄉村工作的認知和理解。
如果要說具體的人,第一個應該是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毛剛強老師。他曾分享了很多鄉村的實踐經歷,教我們怎麼在村裏推動村民組織的工作,讓我開始明白社工在「讓大家組織起來」這件事情上的作用和角色,以及「組織起來」對村莊的意義。
第二個應該是李麗老師及其團隊伙伴。之前李麗老師的實踐主要在貴州,我曾拜訪過她以前工作的村寨,感觸最深的是一個位於麻江縣的村莊。當時我只是抱著好奇的心態想去了解他們的工作,到達後分明感受到村民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對參與學習、參與村寨文化傳承的熱情,與此同時也了解到大家在面對生計、面對主流價值選擇的無奈。那一刻,似乎更加深刻地體會到鄉村社工這個身份。可以想像當時李麗老師和團隊經歷的困難,甚至有說法覺得撤出、結束項目是一種失敗。但是很奇妙,我感受到的卻是李麗老師和團隊行動留下的力量——當年播下的種子開始發芽、成長。這種奇妙的體驗可能很少人能理解和體會,卻增強了我對自己作為一個鄉村社工的自我認同感。
對照三年前,你覺得自己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如何成就了現在的你?
回想起來變化還是很大的。三年前,我還沒有想清楚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喜歡做什麼、擅長做什麼,只是把社工看作一份單純的工作。而現在,我對作為一個鄉村社工的自我認同更堅定了。三年來在村子裏的生活、工作,與村民的對話,豐富了我對社工的理解,讓我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不再那麼狹隘、封閉和驕傲。
自己平常工作中會經常走訪村民,特別是條件困難的老人、兒童。作為社工,我需要傾聽大家的各種遭遇和困難,有些會讓我覺得是命運的不公對待。但很有意思的是,在家訪裏我感受到更多的不是他們面臨苦難的無奈,而是這些「被邊緣化」的人們對生活的韌性——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樂觀,大家都盡己所能,努力、堅強地過下去。
底層老百姓對生活的熱愛,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為之所付出的實際行動,深深地感染了我——如果家訪的對象換成是自己,我會怎麼做?堅持嗎?還是放棄?這些經歷讓我明白——與其抱怨不公,不如樂觀面對,付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動去改變自己的處境,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療癒自己、堅定內心方向的寶貴經歷。

村裏的我們:找到自己的位置
根據你的體驗和觀察,你覺得鄉村社工的理想狀態是怎樣的?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狀態?
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既能紮得下來,又能和村裏人一起做有意義的事情。我先分享自己真實的感受,然後再來看什麼是理想的狀態。
今年在雲南昆明近郊的一個村莊開展工作,似乎對駐村有了更多的感觸。村莊不大,人口分佈很集中。駐村以後,我和大多數村民都建立了很好的個人關係。但是最近這種關係,或者說和大家關係都很不錯的狀態,也會讓自己背負更多責任——作為一個社工,必須和大家一起做點什麼事情,去回應大家面臨的問題,比如組織媽媽學習兒童管教、組織老人建立老年協會等,這些事情本來也是工作計劃的一部分。
然而,我好像並沒有很好地和大家一起坐下來聊過這些事情,和大家的關係似乎僅停留在「認識」「熟絡」的層面,卻沒有太多一起「共事」的經歷,沒有達到一種理想的狀態——和大家有更多深入的交流,一起做一些大家想做的事情。作為社工,我想和大家一起服務村莊,但村民會認為,他們是給社工幫忙的,這讓我覺得很難過,這樣的理解偏離了我作為社工動員大家一起做事的初心。有時候我會把原因歸結為太忙,但更主要的原因在於沒有和大家形成共識——不是社工讓大家做事,而是大家自己要做事,關鍵是村民的主人翁意識、責任意識還沒有建立起來,或者有但還遠遠不夠。
這也引出另一個問題,外來駐村社工怎樣才算「紮根」下來?如果「紮」下來只是工作的一部分,在我看來是很痛苦的,我們和村民的真情實感原來只是一個任務。很難說在一個村莊駐村,自己就真的能一直留下來,如果身心不能安定下來,其實內心是不會真的「紮」下來的——不知道會在村裏逗留多久,也害怕不確定的事件,讓一些行動不能持續,然後就沒有了行動力。
所以,回到什麼是理想的狀態這個問題,我認為,如果一個鄉村社工能讓自己很好地「紮」下來,比較好地處理自己的定位與角色,讓自己的內心能安定、安寧一些,然後和大家一起行動,是一種理想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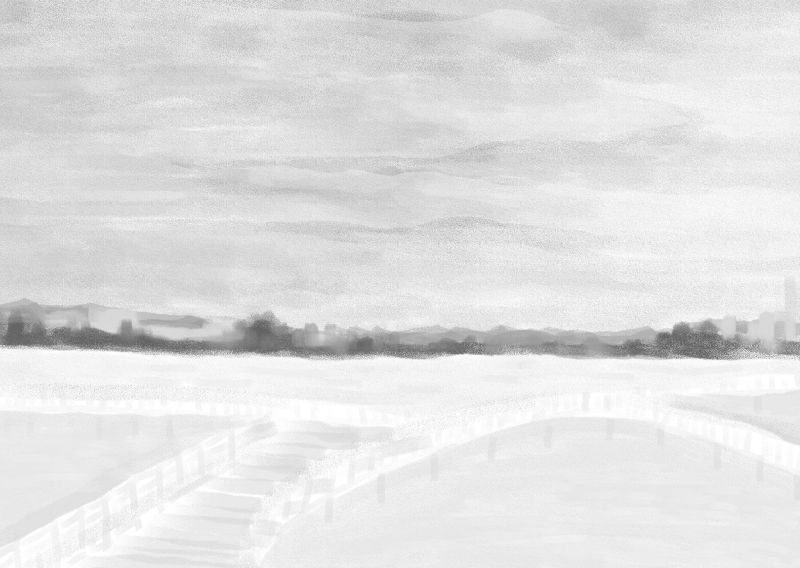
村裏村外:在村裏,活起來
在你看來,鄉村社工和返鄉生活者有什麼異同?
不同有很多,角色身份不同,導致大家思考問題的視角也不太一樣。最明顯的差異是,鄉村社工在一些行動中更像一個工作者,一個服務提供者,更注重當前的現實情境,因為我們短時間內沒有辦法去了解一個人、一群人的過去及複雜的人際關係。但返鄉生活者的服務行動相對會更加自然,不會表現得像「工作」。作為村子的內部人,返鄉生活者會更多受過往人際關係經驗的影響,對一些事情有更多的判定,更容易產生顧慮。
以貴州清江苗寨的返鄉青年阿花為例。阿花畢業後在外工作幾年,後來決定回村做民宿和體驗遊活動,結合生活中的手工植物染及蠟染、農產品生產加工,召集村裏的中老年婦女在閑暇時共同學習和加工產品,除了增加一些額外收入,也激勵村民重新學習和思考苗族文化保育。
從與阿花的溝通對話裏,我很明顯地感受到她對於引入資源、開展行動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或者打破平衡的顧慮。基於對村莊的了解和對村民的熟悉,她知道大家過去是什麼樣的,現在是什麼樣的,經歷過什麼,從而形成一些無形的判斷。所以,當阿花組織大家一起來做事情時,她會擔心影響了村子本來的平衡關係。當然,一個合格的社工也需要反思行動對村莊各種關係帶來的影響,但多數鄉村社工畢竟是外來人,一方面可能缺乏敏感度,另一方面則是外來人的身份,也許會獲得更多的包容與理解。
在和阿花的對話中,以及昆明大墨雨村的新村民吳晨分享新村民和村莊之間的關係時,大家都提到——要找到自己在村裏的位置和角色,「要有自己的事情做」,做自己擅長的事情,解決自己的生計。當然也不僅解決自己的生計,背後也有自我實現,找到個人與鄉村社會認同的重疊部分。
從他們的分享中,我更深地觀察到社工和返鄉青年、新村民等角色的異同。社工在鄉村裏更多是一個推動者。而返鄉青年和新村民需要直面生計的問題——如何在村莊裏好好地生活下去。這樣的差異讓進入村莊的社工(工作者)更多地側重於服務與活動,生活往往不是主要目的,而返鄉青年和新村民恰好相反,要先好好生活,花很多精力在生計生活上。
之所以審視社工和返鄉青年、新村民的不同,是因為我自己一直在工作和生活之間糾纏。社工的鄉村工作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些指標、做一些痕跡材料就能達到目的,還是需要和村民的生活結合起來。比如,我現在支持婦女團隊編草墩、做手工、重拾舞龍,希望借此促進大家的組織和團聚。在工作者看來這些是指標,但從村民的角度看這些是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需要社工更加用心去觀察和體會,才能更好地找到合作的機會,和大家一起成長。另外,如果沒有共同生活的部分,大家很難建立起信任關係——這是成事的前提和關鍵。為此,我覺得社工融入村寨生活是很重要的能力,也是最大的考驗。
相對於返鄉青年,鄉村社工還需要看到自己在村裏的「不同」,有意識去思考這樣的差異會帶來什麼,但又不能將自己卡在這樣的差異中。比如,即使你想把自己的工作任務融入到生活中,還是會受到外部評價標準的干預,包括項目評估、機構規章制度等。另外,村民對「工作」的評價標準也可能是很主流的,可能會覺得社工平常沒有做什麼——既沒有朝九晚五上下班,也沒有去地裏幹活,但還可以拿工資。在我看來,需要承認與理解彼此的差異,社工有自己的理念、對鄉村的理解,而村民又置身於他們所處的位置,至於大家真的能相互理解、攜手前行嗎?這樣的問題不一定會立馬有結果,但是非常必要,有利於促進我更有意識地理解村民的角度和考量。
在生活和工作這兩個看起來對立的概念裏,我內心會更多地選擇面向生活。生活會讓事情變得慢一點,讓我學會更加尊重村莊的邏輯和倫理(這裏的邏輯和倫理,不是墨守成規,不是看到很多違背社會良心的事情而置之不理),讓大家有更多的空間來審視自己的村莊文化,發掘村莊和生活的美好和價值,然後攜手做一些大家都想做的事情。

你如何理解鄉村社工的可持續生活?
借用《禮記·大學》裏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句話,我的理解是身心安定、安寧後,才能真正堅定自己的方向,才能有所得。
社工是價值取向比較強的職業,一個真正的社工,個人自我價值感給予的回饋是遠高於工資、福利待遇的。這樣的表述看起來很無力、很單純,沒有考慮生活的厚重以及主流價值觀對個人的影響,但我深以為然。自2022年,內心有個聲音一直在提醒自己,除了價值感、收入的支撐之外,還要安頓好自己的身心,滋養自己,才能持續地從事鄉村工作,才能將看起來的「理想主義」變成現實裏的具體實踐。
這樣的理解,是把在鄉村的工作當成一種生活,讓工作服務於生活,安頓好自己後才能持續而有能量地關注、連接他人。
- 龍集文 混跡於西南鄉村的社工,曾供職於多家社工機構執行鄉村社區服務項目,切身感受西南鄉村現狀,由此引發對鄉村可持續生活的好奇與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