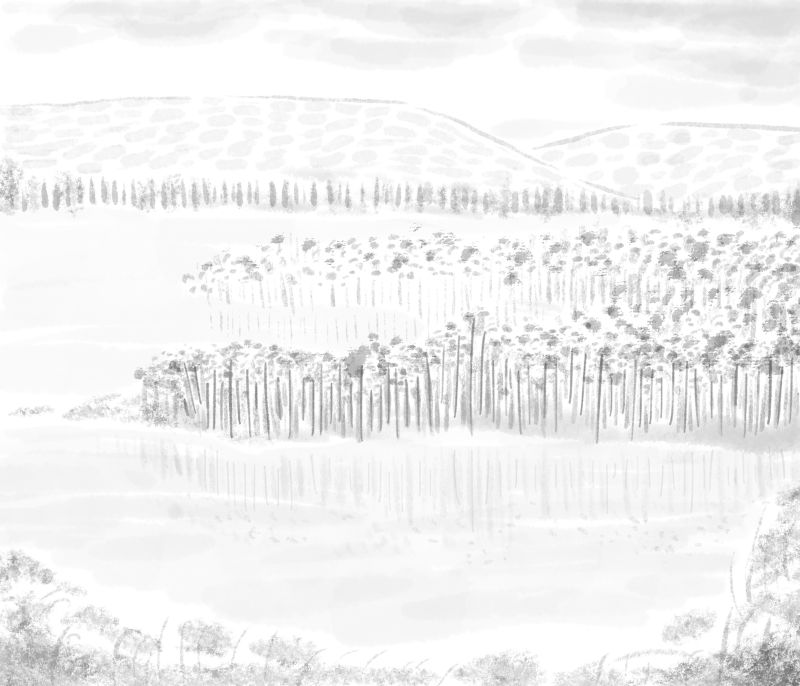文 | 阿樂
都市人與自然環境的距離
2018年9月,颱風山竹吹襲香港,為這個先進城市帶來不一樣的景象:海邊翻起四五層樓高的浪,好些大廈玻璃幕牆被吹爛,整個工程天秤從二十幾樓被吹倒下來......翌日,香港市民如常上班,但不少人發現自己屋苑的大堂堆滿從海裏沖來的垃圾,倒下的大樹樹幹有兩三人圍起來那麼粗,主要幹道嚴重癱瘓,鐵路不通。這次自然災害,是香港三十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切身的影響,誘發不少人反思人和自然之間的距離。
自然建築在南涌出現的契機
朋友傳來照片告知,香港的郊區受災亦嚴重。在南涌,本來安置於魚塘旁的貨櫃宿舍掉進塘裏。另一處的貨櫃廚房被吹翻,導致形狀扭曲,不能再用。還有更多農場的基建被破壞,需要重修。朋友問:「你可以幫手重建嗎?」我知道南涌這個位於香港偏郊的地方,有一群人為著生態保育聚在一起,成立了活耕建養地協會(下稱協會),及後朝著生態社區教育的方向努力營建。我提出:「你們會想用自然建築的方式重建嗎?」就這樣,我走進南涌。但在這之前不無一番掙扎。
為何選擇離開現代建築
我是阿樂。建築系畢業後到香港一家建築設計公司工作,開始了持續四年的規律:從市區的家出發,搭地鐵,步行五分鐘,到辦公室的冷氣房,開始八小時工作;下班以同樣的路徑回家。我最享受的或許是週末,因為可以到郊區行山。現在想來,為何我對每個週末都有如此強烈的渴望?不知會否有人跟我一樣,往山林裏跑,在大海中浮游,其實是在彌補生活中的某些匱乏。我想,如果是一條魚,我會在大海裏有怎樣的一天?
我發現生活在城市的我們,很容易忘記在金魚缸裏的魚,跟魚塘裏的魚和大海裏的魚,本質上都是一條魚。它們不是被觀賞的魚,不是被吃的魚,它們是地球上的一員。
在工作的四年裏,我尤其看到城市空間對這種共同性視覺的缺乏。市區的土地都插滿高樓大廈,公共空間不足。在追崇高效的社會,空間都先讓作功能性的使用。不說人要給車讓行,而是要求容許其他生物共用這個空間,聽起來像天方夜譚。
我選擇放下「以人為本」的視野,離開建築公司,先學做一條魚,摸索是否存在著一種容許各生命體共融地生活的人類建築方式。
在外地遇上另類建築的經驗
到哪裏尋找答案?離職後的一兩年間,我去了多個地方,並覺察到我在建築業所觀察到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問題還有更深層次的根源。
在巴西,我以實習生的身份,進入了當地政府的房屋部門。我被派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的貧民窟,協助部門的公共空間設計工作。耗時三個星期在辦公室做的公園設計草圖拿到社區中心,迎來區內居民的回應竟是:「我們不需要公園,公共空間是犯罪活動的溫床。」我察覺到這種建築設計上的缺失。這種資本主導,從上而下的建築過程,無法回應社區持分者的需要。而重大的問題是,目前這種建築模式正主宰著很多地方的城市發展。
之後到印度的山區,我聯同一個慈善團體為一個兒童之家改造廚房設施。該處的山區沒有集中處理垃圾的系統,每個產生垃圾的單位都自行負責。如何負責?他們把垃圾拉到山邊、路邊、前院或後院露天燃燒。當中有大量不宜直接燃燒的物料,如包裝紙、塑膠等,一些對人體有害且讓環境受損的氣體就直接釋放到大氣中。大家都不以為意,現代的產品有太多是不可被迴圈或降解的。而鼓吹消費的發展模式,太容易使人忘記在過程中人應該承擔的責任。不知不覺這種片面的價值觀滲入世界各地文化。
接著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去了臺灣參與團體「野地森活」的活動,協助建造一家用泥土做的小房子。第一眼看見這個正在建造的土房子,感覺不是特別壯觀,又看不出有什麼創新技術。參與過建造過程後我卻被深深感動。土房子的建造不像現代建築的建造。現代建築建造地基的時候,不論建築物規模,都會先把原本的泥土挖走,當工程廢料送走,然後在土地上以混凝土封住,再在上面建一層又一層的樓房。土房子用的物料無毒無害,現代建築的物料則經常有不少副產品產生:對環境和人體有害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刺鼻的強酸強鹼等。土房子的建築工地裏,沒有慣常見到的大型機械,或到處可見的危險物料。這種環境不期然使人放下警惕,容讓來自更多不同背景和年齡的人參與。臺灣的朋友跟我說,這就是自然建築。
在香港如何做自然建築
自然建築可以在香港發生嗎?
自然建築廣泛的定義是指使用自然材料作為建材的建築物。追求物料是在地的、低度加工、沒有化學添加且可以逆轉迴圈再生的。自然建築同樣關注人的維度,即重視在建造過程中,人與人(建造者與使用者)、人與自然所建立的關係。自然建築運動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美的回歸土地運動(Back-to-the-Land Movement)所掀起,他們在沒有建築背景和資金的支持下,用在地的自然資源作為建築材料,建立自己的居所。
在工作之前,我親身去過南涌三四次。我對這地方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四小時往返市區的車程。直到一天,朋友傳來電郵,說是邀請我參加南涌的市集,並附上照片一張。照片裏是一片藍天和一片綠意。遠處的綠是山脊。山腳處點點白,似是一些小屋。前面的綠一時未認出來是什麼,看見幾個人在草堆裏幹活,應該就是一片還沒長出禾的田。山和田之間也長滿草,幾乎看不出草是從水裏長出來的。之後才知道那是蘆葦。照片應該是初夏拍的,一片綠中隱約泛著夏日刺眼的白光。在電腦螢幕前看到這景象,好美。
沒想到,自己由一位訪客開始,接下了工作,到如今在村裏生活。
工作開初,依然被南涌的自然環境和四時的景物所吸引。不時在勞累的工作過後,走到溪水裏降溫。南涌三面環山,水源充沛。涌口接連沙頭角內海,海浪不大,岸邊長滿紅樹林。春夏的水很多,不少人長途跋涉從市區來,行溪澗看瀑布,看活躍於海岸、陸地和天空的昆蟲等動物。秋冬留鳥和候鳥在溪邊、海岸邊覓食和停留,觀鳥和生態愛好者經常流連。在城市長大的我,開始發現人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大。鄉郊讓我發覺,身邊的環境有更多的物種存在,並以此為棲身之所。我要建築的空間也許不只有人會光臨。
人只是這片土地的其中一員。此刻承載著我們的土地,繼承著過去的痕跡,亦將會是未來的資源。南涌自三百年前有客家人聚居,村落建於山腳,盆地用來種田種地。現在打開地圖看,會發現魚塘的面積比耕地要大得多。這個地貌的改變,源於1950-1960年間,田地被變更為更有經濟價值的魚塘。之後到了2000年代,一反香港城市發展的大趨勢,村中陸續有新的人口進駐。現在的南涌,常住的大概有五六十戶。舊村民大多是退休年紀。活躍於村裏的成員,有幾戶以不同生態友善模式種植的小農,還有做食物教育、身心靈活動的等等。
從2019年起,我以自然建築的概念為基礎,為這個新舊交融、背景多元的社區,嘗試提出另類建築的可能性。在過去兩年多,我協助協會用泥土和竹建造了一個社區廚房,以及一個土窯。
廚房是協會每天都會用到的空間,成員普遍傾向以比較快的方法做一個臨時廚房,並期望在未來的四五年間,協會的整體空間規劃更為完整時,再另建正式的廚房替代這個臨時廚房。南涌有什麼在地的資源可作建築用途?怎樣的施工技術更易為一般民眾所掌握?我記起香港有名的竹棚,不論是幾十層高的大樓的維修棚,或是每逢盂蘭節打醮的戲棚,都能在幾天內完成。在南涌,魚塘就在旁邊,泥土容易獲取,況且有朝一日廚房需要拆掉,泥土也可以直接回歸土地而不污染環境。南涌的另一個魚塘則被蘆葦覆蓋,可以善加利用,除了用作在地材料,也可以削弱蘆葦的蔓延和生長速度。考慮到時間、在地資源、使用習慣後,我提出了一個方案:用搭棚的方式做廚房的結構,草掛在竹架上面,塗上泥土造成牆身,蘆葦用作屋頂和簷篷。
廚房的方案只是個開端,之後的選材、施工和保養,是持續而反復的實驗、驗證和修正,有如各種生命必經的過程。自然建築追求的,不是把自然物料直接應用而不作任何人為添加或改動。如果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以類似的模式工作、運作或回應,我們就更像是一部機器,更不自然,不像我在自然中所見到的到處爬的蕃茄、會游會跳的野豬或會穿州過省的候鳥。對周遭環境及物種有更深入的理解,在建築時使用適切的物料配合技術,是我所理解的自然建築。竹的韌性可與鋼材相比。不過竹糖分高,使用前要花點功夫:經過火烤,可以將裏面的水分蒸發,養分變質,昆蟲不愛;泥土是很好的隔熱物,不過弊端是遇水會溶化變泥漿。石灰塗在泥土上則是天然的雨衣,石灰氧化後可以保護泥土減少雨水沖刷。
對從前的我來說,大自然是一幅美好的風景畫;鄉郊是個休閒、消遣或放下的後花園;而建築是製造滿足人類需求的空間。現在大自然的生物是我會去探望的對象,讓我時刻學習其強大的生命力;村裏的人是與我一起聚餐、工作、生活的人,是互相聆聽和支持的伙伴;建築是在建立容讓更多生命互相交流、共生的環境。
參與者的反思
兩年間,有超過一百人次協助建造。土窯復修則有12個人參與連續八天的工作坊。這些參與者來自不同的背景:有退休的建築師、學生、家庭主婦等,年齡則由18到65歲都有。
自然建築需要身體老實的投入,即使這種勞動使人汗流浹背或肌肉酸痛,但依然有人持續地做。過去一年有一群大學生每月最少來參與一次自然建築活動。什麼驅使他們持續到來?他們的回答很單純:「喜歡這裏能放空,休息,能放下一些負擔和壓力。」面對世界的崩塌和失序,不少人都有種盼望,希望回到如常。一位參與者分享說她在南涌的山水、農田與各位的分享之間,找到一份天地自然之律可以遵循,使人感到心安。
我相信參與者能從這種身體經歷中獲得一種回報:接收來自自然的療癒力量。不論是在處理竹枝或是調配泥土的時候,經常看見參與者對當下工作的沉醉。或許,過往太多的學習是在追求知性的收穫,現在通過自然建築能與自然接觸,促發的是心靈的觸動。這種觸動,也許是反思和改變的起點。
觸動使人意覺人不再是獨立的個體。人的關懷超越自我。曾經有一位土窯工作坊參加者回饋說,這種學習讓她思考自己作為「人類」的身份,特別是自己在這地球上的角色。土窯完成後,另一位參與者反思:「那燒柴開窯烘麵包會用上很多柴枝又釋出很多氣體,會不會是很不環保的行為?」覺察人的行為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又意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正是改變的開始。帶著這覺察檢視現在的系統,那我們又是否知道電力所產生的污染都排放到哪裏去了?要建造如此龐大的電力基建,又夷平了多少村落,影響了多少家庭?
我下潛到大海裏,尋找我心中樂見的魚兒。我看見有一些魚的容身之所就在海草或珊瑚之間;魚成群地覓食;魚的食物來自其他的生物,而它產生的廢物和排泄物又成為其他生物的養分。魚的生命得以維持需要依靠互相貢獻、互相成就、合作和支持。這是我在一條魚身上學到的。人為生活所需而消耗和建造無可避免,但我們在獲取自己所需的同時,是否可以多一份對其他生物的貢獻?我希望人類的建築方式可以朝向更為低生態負擔的方向發展。參與自然建築的活動也許是讓自己保持著這一份生態觀念的覺醒:人與各種生物互相依存。當更多的人保持這份覺醒,積極地在各自的領域做出行動,我們的生活狀態和生活環境就有改變的可能。
- 阿樂 自然建築實踐者與導師,定居於香港南涌附近的鄉村,除了建築,有時還會跳舞和做麵包。